第二十一节
在大寨参观的那几天里,郑仙巧意外地遇见了自己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同学、后来转学到了北京、现在已经在山西插队数年的任鸣鸣。
两个人是在一次两支参观队伍在回程中相遇时碰面的。
在参观大寨的队伍里,知青共大的学员队显然是一支最年青的队伍。像这样一水儿由知青组成的参观大队,不知是不是绝无仅有,反正肯定是不会多见。因此,这支队伍无论走到哪,都挺“扎眼”招人的。其他以各地农村干部为主组成的参观团见到了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时,往往都忍不住要驻足观察一下,也有不少前来询问的,因为很少见得到任何地区的农村一下子会有这么多年青干部聚集在一起的。在中国的那个时代里,绝大多数农村干部都是从闹土改的时候就上了任的,一个村里能有个把参军复员回来的干部补充进来就已经很不错了。即便已经经过了“四清”和文革两次大型的“吐故纳新”,年青干部在村里、尤其是各村的主要干部中所占的比例还是不大。这几年,一些生产队从知识青年里提拔了一批社队基层干部,总体上仍然只是沧海之一粟罢了。因此,当任鸣鸣与自己的参观团一起遇到了知青共大这支队伍,又听说是来自内蒙古的知青参观团时,当然不免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上前询问是否有自己原来中学的同学。
这一问也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北京这边的同学没找到,却遇见了郑仙巧这个自己在天津时的老同学。
任鸣鸣非常兴奋,他立即向自己团的带队团长请了假,随知青共大的队伍到了他们的驻地。与大家共进晚餐后,郑仙巧为任鸣鸣专门组织了一个讨论会。她先请任鸣鸣为共大学员们介绍了自己在山西插队数年来的实践经历,再请任鸣鸣向学员们尽情提问,由大家进行讨论和回答。
任鸣鸣所在的村子里,一批下了数十名北京知青。七八年过去了,现在全村只剩下已经担任了生产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他自己、和分别担任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职务的不多几名知青了。大多数知青都被县里安排了工作,回北京的知青并不算多,而且大多是办“病退”回去的。
“我有个感觉。是这次来参观后产生的。以往在队里,觉得咱们知青上山下乡,已经给中国的广大农村带来了明显的大变化。可来这里一看,就说这么多参观团吧,它的成员构成里根本没有几名知青在其中。这说明了什么?还不是说明了中国广大农村真正的主力军仍然是八亿农民嘛。咱们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下来了,比起八亿农民的数量来,还是少得可怜啊。过去宣传中总是讲咱们是生力军,那时候觉得提得还不够劲儿,现在一想啊,咱们能真的够上生力军就不错了。客观上讲,对咱们知识青年来说,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有许多种,至少比八亿农民多得多;再加上咱们的知识和阅历相对说比八亿农民的大多数要强上一点点,党中央毛主席又对咱们特别给予了明显比一般社员们高得多的实际关怀,这才使咱们知青的个人发展道路上出现了许多比农民社员们、至少是与咱们大体相同的回乡知青们多得多的机遇。因此,我觉得咱们知青千万不能自己就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不能觉得自己就真的比那些长期生活在农村的朋友们高一头,而是更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夹着尾巴做人’,这才能在咱们扎根农村的伟大实践中真正做出一点成绩来。”任鸣鸣向知青共大的学员们发出了这样一通感慨。
“是啊,我这些天看见的来大寨参观的队伍,尽是些半大老头子,连女干部都不多呢。”一名女学员也感慨着搭了腔。
“这个问题提得好。不过,我想大家还应该想到另一层意思。”黄念生忍不住要发言了。
“哪层意思?”郑仙巧问他。
“我是在想。知青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八亿农民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基本事实。主力军和生力军的差别也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但这不也恰恰说明了咱们这批知青更加‘任重而道远’了嘛。正是由于人数少,因此,咱们每一名知青所担负的历史重任就更加沉重,每个人都更加应当努力发挥出自己一切可能的光和热,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第二故乡更多地做出一点什么来啊。想当初红军长征的时候,到达陕北的只有区区三万来人。这比起当时全中国的四亿多人口来不是更少了吗?可就是这三万多人,为中国的明天指明了方向,引导和带领着中国广大劳苦大众完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起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咱们知识青年虽然不是无产阶级的先进政党,却是这个党所领导的一支重要年青力量,我感觉我们就应该像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那样,把自己锻炼得真正够坚强、有力量,党指向哪里,咱们就能打到哪里。当年,党需要她的战士们解放全中国;今天,党需要我们在广大农村牧区改天换地。这都是不同历史时代对青年一代的召唤啊。同学们,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一点儿不比消灭国民党八百万大军容易。毛主席说过,新中国的建立,不过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而消灭三大差别的战斗,则是需要几代人的顽强努力才能够得到完成的更加伟大的历史任务啊。在如今这样的和平年代,有许多物质上和精神上的东西在诱惑着我们青年人,三大差别本身就使人容易产生向往城市、而不愿在农村牧区坚持艰苦奋斗、大有作为的思想和实践倾向。再加上城市本身也需要大批青年人接各方面的班,‘扎根’就更加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了。而咱们知青共大呢,就是在做着这件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壮举,咱们这批学员,就是要在这个时代里走出一条新的长征路的英勇战士。任鸣鸣同学讲的‘要夹起尾巴做人’一点也没有错。但咱们不能把它理解为可以因此就对自己放松要求了。实际上,咱们的任务、咱们的责任都是更加重大了。今天听了任鸣鸣同志的发言,再加上咱们在大寨参观的感受,我觉得咱们大家都应该更加认真地考虑一下自己毕业回去后应该做些什么这样严肃的事情了。大家说对吗?”原来,黄念生听了任鸣鸣的发言,感觉他的调子有点低,怕学员们受到反面影响,于是赶紧插了这么一大段议论。
当晚,任鸣鸣与郑仙巧又促膝长谈了整整一夜。两个同是知青出身、又同样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的老同学,在大寨这块中国社会主义农业最神圣的土地上,畅开心扉谈了很多很多。
谈话中,任鸣鸣对黄念生的思想认识觉得过于激进,而郑仙巧则一力地为黄念生作着解释,向任鸣鸣介绍小黄的经历和为人。任鸣鸣反正也不认识黄念生,又不打算与他共什么事,只不过是有感而发的议论,听了郑仙巧的解释,就不再说它了,笑了笑,就把话题转开了。
当然,两个人谈得最多的,还是对如何尽快改变自己第二故乡面貌的经验交流。两个人都从自己的实践中深深感觉到了掌握现代农业科学知识和技能的极端重要性。也深深感觉到了要在自己的第二故乡普及这些农业科技的严重障碍和极大阻力。对于自己个人的前途,两个人都认同“将来肯定得到公社或县里发展”的基本趋势,因为这是一个既能保证自己选择的事业能够继续进行、又能保证自己个人的基本生存的最实际趋向。两个人都觉得,如果上山下乡运动能够正常继续下去,那么知青们未来的实际出路,除了一部分肯定是回城参加新的工作外,应当是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第二故乡所在地区的公社、县乃至地区三级担任各种职务,而留在队里一辈子的知青在人数上恐怕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不是理论分析的结果,而是二人从各自的长期实践中得出的一种结论。
特别有意思的是,虽然两个人都是由于参观大寨才得到重聚机会的,但在二人这一整晚的交谈中却几乎没有涉及过学大寨的话题。两个人谁也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对,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是否说明了什么问题。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是黄念生的那一通发言,使得不少在参观大寨过程中产生了思想疑问的学员们反而在“认真思考自己回去后怎么干”的问题上,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疑虑。因为,问题一接触到自己队里的实际时,那些自己虽然认为已经接受、然而却远不够成熟的理论就受到了最强烈的对抗,许多自己认为难以解决的实践性课题都跑出来搅和自己的思维,反而把自己的思想搞得更乱了。
总之,学员们出发前的高度兴奋,在大寨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多数学员对大寨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因为他们总觉得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自己的所在队与大寨实在是差到了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任凭自己决心如何大、信心怎么强,最后怕也是要学习不成而白费功夫的;一些比较朴实的学员得出了“‘幸福不会从天降,不下苦功花不开’。最重要的还是要真心真意地坚持长期艰苦奋斗”这样的结论,他们对于这次大寨之行还是相当满意的,不过,他们实际上也并没有得到多少具体的收获;几名最“革命”的学员则得出了“大寨好就好在有一个真正革命的领导班子”的结论,下决心回去后不管怎么样也得先把队里的大权夺过来,然后才谈得上学大寨;更有如刘惊涛等自主意识特别强并有相当实践经验的学员,由于自己的独立考察和思考,干脆对学习大寨得出了“不能再盲目学习下去了”的结论,开始独立自主地去寻找另外的经验和模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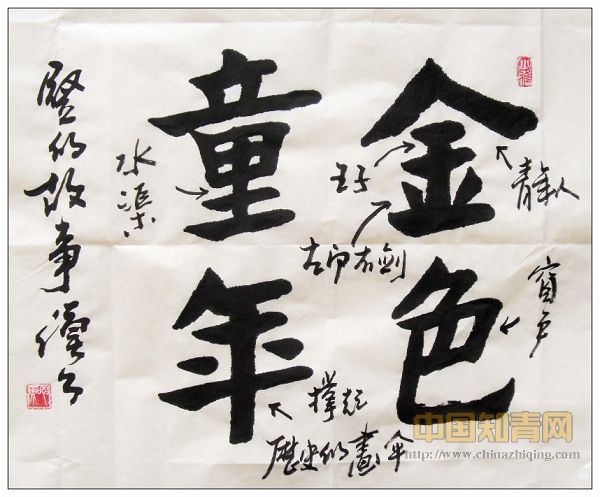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2/2/22 15:1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2/2/22 15:1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