斧劈壮阔
山水画打开了水墨技法的大门,活力倍增,发展势头不可遏制。由于淡墨的 积累有一种厚重的体积感,画山石能刻肖逼真,在墨线的轮廓里,以淡墨点作皴的画法,对于北方山水极为合适,这种写实性很强的山石皴法,在荆浩笔下已露出不凡的英姿。传为荆浩所作的《匡庐图》,名目为南方山,实质上是典型的北方山。嵬伟陡峭,山体石骨显露,其中的皴法,不时用浓淡相交的短笔皴,加上适度的墨水渲染,大山凸现,可敬可畏。在荆浩之前,尽管出现多样的写实方法,尽管有如张那样形神俱盛、情意交融的山水画大家,但和荆浩相比犹逊其色。
可以说荆浩是强调笔墨技巧和真山水完美统一的第一人,他的突出成就,便是开拓了水墨技巧的写实性。假如《匡庐图》真是出自荆浩之手,其成熟程度当令人惊叹!
荆浩造就了宋初三家,确切地说,是造就了宋初北方山水画的三大流派。关仝、李成、范宽,都是承接荆浩衣钵后自开门风的。其中关仝的短笔,化解了荆浩的点皴,笔和墨的交融有所加强,墨韵出色,却减弱了笔力,高爽的气质里不免夹杂着萎颓;李成发扬线皴的优长,但这种线皴是有限的,它短而曲,隐隐约约可见点皴的影子,轻盈灵动,变化多端的短曲线实在太文秀了;范宽恪守荆浩遗风,妙在能变,又妙在能给后世以变异的基因。
画史上都称范宽是学李成的,不知以何为据,但北宋的史料上众口一词,不由你不信。当然最令人信服的是范宽的悟性,他认为:“前人之法,未尝不近取诸物。吾与其师于人者,未若师诸物也。吾与其师于物者,未若师诸心”(见《宣和画谱》卷十一)。这话灵性剔透。倘使他在李成身上学到些什么的话,以此论来化解,则必不输于李成。其实,从现存的范宽遗迹来看,他是取荆浩的、关仝的为多,尤其是荆浩的点皴,在范宽手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范宽的特点就是点皴,范宽的风格就是以山石的点皴和鹿角树形构成的关陕山水风情。范宽开创的点皴,即著名的雨点皴,也有称其为钉头皴的。这两种相近却稍见不同的皴法名目,道出了范宽点皴的形体变化。
雨点皴,犹如雨点。范宽惯于作巨壁式的高山悬崖,大面积的山体,用密密匝匝的雨点状的皴法,并不像雨淋墙壁那样麻点一片,而是需要在点与点之间出现呼应,对比的关系。因此,范宽是以淡点的积聚,以小点的形体变化,从局部到整体,有条不紊地在层次上显示其丰富性。淡点之间有排列,有重叠。钉头皴则是上阔下狭的点皴,阔狭的幅度不大,但这细小的变化,于千点万点之下,效果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雨点皴和钉头皴,都有效地表达了山石坚硬、厚重的质地感和体积感。
如果说李成的卷云皴和蟹爪树,因笔法上的相似而营造出李成特色的话,那么,范宽的点皴和鹿角树以及山顶类似点皴的密林,则也是因笔法类同而建立的范宽风格。李、范两家成为北方山水画的代表。范宽又于雪景独占鳌头。范宽的雪景和点皴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淡墨点簇聚为山石写貌传真,将淡墨点再放淡,改簇聚为稀疏,多作留白,烘染天白、水泽,则是出色的雪景了。还有,范宽的点皴又给他特有的山水结构带来了方便,范宽的山水画构图以大块的面取胜,往往是,劈面巨的峰高耸,用点皴的小面来堆积成峰的大面,是明智的。他只须将大面切割成几个自然的凹凸面,由点皴来处理凹面,可得面面俱到的效果。大结构用小点皴作实质性的具体描写,聚小而见其大,在大势的笼罩下,小点皴不但不嫌琐碎,反如千军万马般地增添了气势。
范宽的点皴和鹿角树法,为他赢得了“真石老树挺生笔下,求其气韵,出于物表,而又不资华饰”(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卷二)和“峰峦雄浑,势壮雄强”(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的赞誉。米芾也盛赞范宽说:“本朝自无人出其右”,“物象之幽雅,品固在李成上”(《画史》)。但又有微词:“范宽虽雄杰,然深暗如暮夜晦暝,土石不分。”并认为这是“晚年用墨太多”所致。我们没见到过似“土石不分”的范宽作品,无法判断米芾对范宽白璧微瑕态度的是与非。不过可以揣测范宽“土石不分”的晚年之作必有可观处,抑或是在追求“土石不分”的浑沦效果。试想,土石分明作为写实状物的形似角度来说,固无可挑剔,若以土当石、以石为土,两者交融而上升为笔墨上的化境,则实在应视作为范宽晚年达到的一个新的艺术高峰,可惜我们无缘睹其盛。米芾作为一流的鉴赏家,竟没有品出至佳的趣味来,也是极为遗憾的。
山水画最重视皴法的运用,五代至整个宋代,是创造皴法的时代,也是在写实性上运用皴法最完美的时代。纵观皴法,无外乎点、线、面笔墨的具体表现。北宋初已具备了点皴和线皴的规模,南宋初的面皴,是点皴的扩大化结果。这是由李唐领格的南宋水墨山水画风,它将山水画带入一个新的天地。
李唐的一生,大部分是在北宋度过的。《万壑松风图》,是他南渡前的作品。这幅绢制的整匹巨作,倾注了李唐的心血,可以看出皴法变革的种种迹象。皴法变革的缘起,固然有造化上的因素,但究其实质,还应从空间观念的变异出发,因为自宣和过渡到建炎、绍兴,山水画就萌动着空间的变异,很难认定南宋的变革是地理的迁移。北宋的全景式构图,是一种大空间大结构大技巧大意境的制作,其空间结构和技巧混合成一体。北宋中晚期,画家们抒情意识有了提高,强调景物亲切、感人,因而近景被凸现,得到强化,如赵令穰的《湖庄清夏图》,已是小景化的手卷构图,相应地,技巧也出现了变化。《万壑松风图》,虽然可称煌煌巨制,但无全景式构图那般周全、细密的景致程式。它以松林和正面的大山为主景,直率地突出景的视觉效果。这一点又要溯源于范宽了。范宽的正面大山纵有压顶之势,尚在山脚与中景、近景之间留有余地,而《万壑松风图》则直上直下不留余地,效果之强烈是空前的。
在画法上,李唐也不能依照范宽式的点皴那样全用湿笔小点,那样密密排列,那样互相照应有序。空间的观念变异必然会引起笔墨技巧上的变异,李唐只是在钉头皴上稍作改变,他扩大了钉头皴的面积,强化了钉头的头部,改变了笔势的倾向,增加了笔致的干湿对比度,提高了墨色的变化层次,丰富了顿挫间的感情色彩。可以说,李唐的《万壑松风图》,无论从构图上看,从笔墨技巧上看,都是独树一帜的。
这已足以掀开崭新的一页了。但他又急切地掀开了更新的一页,那是李唐南渡以后的业绩。
看过李唐南渡以后的作品,几乎被更新鲜的画风掩盖的《万壑松风图》,只是南宋水墨山水新风尚在北宋画院里的一次尝试。被强化的钉头皴还属于点皴的范畴,但已开面皴——斧劈皴和刮铁皴的先河。假如没有靖康之变,李唐安居于宣和画院,那么,也许不会出现以斧劈皴为代表的南宋院体水墨山水画体系。但李唐的画风肯定会依照《万壑松风图》所显示的变革倾向继续下去。面皴的端倪已露,发展也必有可观处。南渡给画家一个发展的良好机遇,南方的山水风情和偏安的心理,划出了政治、王朝的时代,也划出了绘画发展的新时代。
李唐的功绩是巨大的,他成为整个南宋山水画所谓的水墨苍劲派也即以面皴为特色的山水画的鼻祖,是毋容置疑的事实。这归功于他的创新精神,归功于他写实的敏锐感觉。但是,在李唐以外,与李唐同时或略早于李唐,山水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已经悄悄地变了。它并不像李唐《万壑松风图》那般强劲的刮皴;越令穰就以墨线勾勒下的烘染再加细点来代替线皴,赵佶画卷云皴也加强了点子的分量。重要的是北宋晚期的山水画构图并不再热衷全景式了,这是面皴得以在南渡之后迅速发展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铺垫,半边一角的构图程式加面皴,是典型的南宋水墨山水风格,即使像传为李唐所作的《长江万里图卷》那样的大作品,也只是半边一角式的构图的连缀,它完全没有先前全景式构图的空间容量,面皴以其墨块墨色夺人心魄的表现力来传神的。南宋的水墨山水小景真有咫只千里的写实魅力。
肖照是李唐的弟子,传世的山水画作品大概仅存《山腰楼观图》了。看得出他处处以乃师为楷模,一点一画都在李唐的窠臼之中,他画出来的山石如铁铸一般,坚硬凝重是自不待说的,然而笔致缺乏灵动,显得板滞。由于变化无方,皴法的堆砌使得画面沉闷。作为李唐画风的影响者和推广者,作为最早的以面皴为主的画家,这种瑕疵是可以原谅的。
后世称“南宋四大家”,指的是刘松年、李唐、马远和夏圭,似乎前三位都兼工人物画同时也能作青绿一类细密工致的山水,尤其是刘松年。可见,所谓的“南宋四家”,并不尽是擅长水墨山水的,又可见南宋的山水也并不是水墨山水的一统天下;但是谈论面皴,却必然是水墨山水的专利。在刘松年人物画的配景中,我们可一睹他面皴的风采。《醉僧图》是刘松年淡彩工笔的人物画佳作,他极为工致地描绘松树,在松根处坡石的处理上选择了面皴,为了和松树的画法保持统一,其面皴不作明显的斧劈,而是将轻刮和渲染浑成来表达似土似石的效果,很是别致。另外,刘松年《四景山水图卷》中出现的斧劈皴,温和清敦,不时加入渲染,他小心翼翼地追求工笔和斧劈皴的一致,因此,少了粗犷,多了刻画的痕迹,皴法略嫌琐碎,然而他能把属于水墨山水画法的斧劈糅进工致细密的格式中,是独具匠心的。同时也能看出李唐那种新兴的画法受到了普遍的欢迎。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斧劈皴的代表人物,当推马远。马远和夏圭几乎成为南宋水墨小景的领衔画家。一角半边的构图程式被嵌入他们的姓后——马一角、夏半边,又几乎成为马、夏辈的专利。也有把斧劈皴分出大和小,以区别李唐和马远,称李唐的画法为小斧劈,马远则是大斧劈了。其实,小、大之别,并不能说明李唐、马远之间的差别,在斧劈、刮铁皴的笔法上,李唐无论在气势上还是在韵度上,都要胜出马远一筹,运笔的精到和墨法的细致更是南宋其他画家所望尘莫及的。但是,马远也有长处,斧劈皴传到他手上,各方面的条件均已成熟,他是躺在诸人成果上作极致推进的画家。他在淘劣汰芜、取精用宏的本领。马远的小景,笔致略显干燥,尤其是纸本的小景,这种优势就更加突出,当然,马远的干笔不可能像元人那样地讲究书写的效果,他相对地在他那个时代能见干毛,
已超人一等了,笔法简括再加上拿手的水墨渲染使得画面滋味十足。《踏歌图》,是马远的佳作。他极注意画面的调度,同样是斧劈皴,此图中是一种收敛的姿态,说是收敛,实在是蓄势,寓放于藏,他皴得精微,刮得细致,又于精细中略展势头,远山的真皴,雄强中得清刚之趣,横皴几道,小心翼翼,亦见功力。斧劈皴的排列体现了他十分高深的绘画修养,于是他可以更精细地做些文章:双钩竹偃仰起伏;田畦中的稻菽也丝丝入扣;涧水在乱石奔流,与踏歌唱丰年的农人共欢。《探梅图》是粗犷的画法,其斧劈皴中充满了豪情,笔法上没有大开大合,却凝重浑厚,倍见森严气象。马远用斧劈皴的手法老到,他能根据意境去设计出不同的方法。斧劈皴能别开生面,马远功莫大焉。
夏圭也是接斧劈皴衣钵的画家,却受另眼相看,后人称之为“拖泥带水皴”,是斧劈皴基础上的改良物。夏圭的皴法,比较讲究墨色的浑成效果,他于笔法中渗入破墨的方法,笔未干即用水接,或于湿处再皴,笔和墨交融,就出现了似土非土似石非石的土石混交的模样。拖泥带水的名目或由此而生;或与笔迹墨迹分明的刮皴相比较而得名,这只是依样揣测。总之,夏圭和马远不同,和李唐更不同,这就是南宋水墨面皴的传递和发展,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使之完善,为后世树起楷模。
一入元代,新的山水画审美潮流,几乎将南宋以斧劈皴为代表的水墨山水画扫荡殆尽。然后,仍有面皴的珠丝马迹。别的不说,光是元四家中的两位巨匠——吴镇和倪瓒,就向我们透露出南宋余绪的信息。吴镇虽然以披麻皴为主,却有运用刮铁皴的嗜好,这种称之为刮铁的面皴,在吴镇手里,出神入化,他小而轻,力量不弱,加之渲染得当,加之苔点——芥点、圆点的掩护,出入得十分书卷气,最重要的是吴镇把刮的笔法进行了书法化的改进,因此多了文气士意,少了敛拔弩张,适应了新的绘画审美。倪瓒的折带皴,是面皴和线皴的结合,他先学董源、巨然,自出风格后,把折带皴托名为从荆浩、关仝中来,这样做,不是为了炫耀渊源,也是出于避南宋的嫌。实际上,他的笔法是刮和拉的混合体,说到底是披麻皴横处,以刮铁皴作头或收尾,只是干毛轻盈的笔致与南宋的面皴大相
径庭。高手都有点铁成金的本领。
明代承宋制,恢复了画院,并且连画风也一并恢复了。在元代几乎绝迹了的斧劈皴,又风行起来。原因很简单,明代的开国皇帝没有什么文化,又痛恨“胜国遗风”,他心里想的皇家画风只有宋代院体画。洪武时期对文人画家的迫害是骇人听闻的。
王履的《华山图册》,画的是西岳华山的实景,尽管不时地暴露着文人画的某些气息,但在方法上,他很谨慎选择了斧劈皴。王履是位注重写实的画家,他放弃了元代纯以意为主的观念,用宋人对大自然的体验和襟怀来表现大自然,由于该图册是纸本,所以淡雅和苍劲兼而有之,“心师目,目师华山”的写实倾向溢于笔墨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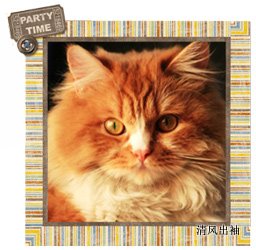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11/23 22:4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11/23 22:4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