斑驳的身影
看了网上的一篇写疯子娘的文章,心在流泪,在激动,在感慨,于是想起了多年前的一幕。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晚饭后,人们都在院子里乘凉。忽然人们都往村子南头跑去,原来是来了一对行乞的夫妇,女人还是个疯子。于是也随人群到了那里。这是生产队曾经的队房,因生产队体制的消失,而沧桑在这里。这是两间破烂不堪的房屋,经年失修,墙皮也落得一片一片的。屋顶的角落还直立着几根荒草,在夕阳中摇晃着。房前已围满了人。只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手舞着一串竹板,正在向人们振振有词地念叨着。一个女人,看起来也就是二十来岁的样子,梳着不整齐的剪发。虽然满面尘垢,但可以看出她的皮肤很白,脸色也挺红润着。虽然衣衫破旧,也掩盖不了她年轻的气息。此时的她,正对着斜投在那堵破墙上的一堆夕阳,两臂平举,仿佛燕子在飞翔似的舞动着。她一边跳着,嘴里还时时地发出“妈吆”“妈吆”的声音。我望着她那斑驳的身影,心里涌起一阵怜惜,一阵酸楚。听周围的人说,这是一个疯姑娘。她的父母将她送给了眼前的这个行乞的男人,于是,她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行乞的疯女人。
人们出于对这个女人的怜悯,于是就把一碗米半碗面的,都装进了那个男人的脏布袋里了。后来,那对夫妇就住在了破旧的队房里。以后的好几个黄昏,这里重复着同样的一幕。再后来,人们也不那么热心,那么好奇了。于是,不知哪一天,这对夫妇在村子里悄然消失了。
记忆中似乎是过了好长的时间,这对夫妇又出现在村子里了。那个男人还是那个样子,可那个女人的变化却是那样的大。衣衫更褴褛了,头发蓬乱,面庞也失去了红润,憔悴了许多,只是肚子明白地隆起,显然是怀孕了。而且人们也知道了她的名字,喊她“tang板仁”(“tang”,这里方言是说“傻”的意思)看来那个女人叫“板仁”。人们虽然也接济他们,但也不像以前那样去围观了,只是那些孩子们时而跟随着tang板仁,戏弄着,欺侮着,有时大人也会出来阻止。渐渐地,人们也习惯了,tang板仁的存在也慢慢地与人们无关了。只是听人们说,在那间破房子里,夜间经常会传出女人凄厉的哭喊声,可也没有人去理会。不知什么时候,这对夫妇又离开了,也没有人再提起过。
又过了一段时间,那个男人又出现在村子里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人们传说纷纷,有的说tang板仁生孩子死了;有的说是那个男人把她丢弃在五里明沙了(五里明沙在库布其沙漠的边缘)。总之,tang板仁是彻底地消失了。
这么多年来,我只要回到那个小村庄,看到队房的那些破壁残垣,总会想起那个tang板仁。那间破烂不堪的队房,就像一位目睹世事的老人,在岁月的静默中见证了一个疯女人从出现到消失的短暂的过程。Tang板仁,一个在落后愚昧贫穷中,从身体到心灵深受着双倍蹂躏的疯女人。在她那短暂的人生路上,铺满了坎坷与荆棘。也许,这最后的彻底的消失,也是她苦难人生的一种解脱吧!
Tang板仁,一棵任人践踏的荒草!一个在痛苦中泯没的可怜的疯女人!她那斑驳的身影,她那声声的“妈吆”,与那两间更逾破烂的队房一起,见证着一个曾经的故事。
(07·7·16)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0 8:2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10 8:2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0 10:0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10 10:0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0 10:5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10 10:5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0 12:0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10 12:0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21 16:2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21 16:2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22 20: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22 20:48: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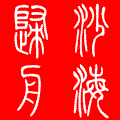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22 20:5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2/22 20:5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