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茬子
打茬子
刨茬子、打茬子是大地解冻后春耕春播开始前的活计。茬子,是庄稼收割后遗留在地上的短根和茎。茬子的“茬”,字典上读音为“茶”,科尔沁人读作“炸”。刨茬子,就是把收割苞米后遗留在田垄里的根茎抠挖出来;以便春耕起垄,播种入土;还能获得一批好柴禾;打茬子,就是用力磕净苞米根系上的“护芯土”,这样做,柴火好烧,更重要的是有效防止田野土壤流失。否则,年复一年,每个茬子根带走一大坨宝贵的团粒结构富营养土,那耕地损失就大了。
刨茬子的人,双手一前一后握好镐把,镐头探在身后,顺垄前行,侧身回头,镐抬镐落,把苞米根须斩断。看剪影,就像古战场上武将交锋,使用拖刀计、回马枪,立斩顽敌首级,动作干净利索。
在影视片里见到过油田专用采油设备——“磕头机”,机械臂在相等的时间间隔里,永不知疲倦的重复同一个机械动作:抬起——落下。田野里刨茬子的劳动力,好比轻型的顺垄沟移动的人工“磕头机”,一天成千上万次等间距(株距)有节奏地镐起镐落,斩断苞米茬子的须根,全靠血肉之躯,全靠肌肉发达的臂膀,全靠一身蛮力和坚忍不拔的意志。
刨茬子要比铲(锄)地累得多。一是刨茬子用的马蹄形镐头要比铲地的锄头重许多;二是铲地只是在地表皮上松土、除草;而刨茬子要斩断苞米扎进土垄的密匝匝根系。刨茬子握镐把不得法,掌心会打满血泡,不小心磨破血泡发生感染,形成了“膙毒”,麻烦更大,需要手术引流排脓。刨茬子手法不对头,难免受瞎累,简直就是用镐头连续翻动大土坷垃块,属于超强的体力劳动。科尔沁一度推广苞米“大步双株”密植法,一埯留两株禾苗,刨茬子的工作量翻番加倍。没有经过长期历练的生手,连着几天刨茬子,会被累得腰酸臂痛手胀腕子肿,甚至尿血。
茬子刨倒后,撂在垄上,经过晾晒,自然风干,护芯土变得疏松了,较容易磕打。
打茬子的活儿,骑垄跨步,马步蹲裆,面向黄土背朝天,两手不停地抓起一对对苞米茬子茎管,用力对磕。打茬子一般都是大风呼啸、浮尘漫天、“土地爷请客的日子”。偏偏干的活儿又是自讨苦吃——抖楞土坷垃。尽管采取了看风向站垄,包严头巾,扎紧围脖,带好风镜,以防风沙迷眼等种种防范措施,穿裆风倒卷浮尘,仍难免弄得个个灰头土脸,累得直不起腰。当地农谚说,“女的怕补袜子,男的怕打茬子”,此话不假。
磕净土的茬子堆成堆。装运茬子相比打茬子就简单方便多了。用二齿钩子把茬子叨到筐里,扣到车上,铁锨一拍,茬子们盘根错节,相互咬紧,不用绳捆索拢,决不会途中散落。
苞米茬子是最受农户青睐的硬柴禾之一。用它烧大灶太奢侈了!拿它点炉子,不必再动刀斧加工,柴禾长短适中;而且火头硬,烧水开得快。盘腿坐在火炕上,喝着苞米茬子烧的开水沏出的红茶,这大概是刨茬子打茬子辛苦付出者唯一能体验到的温馨回报。
听说有些发达国家农业种植早就实行免耕法,庄稼收割后,根系不用刨挖捡净,就地翻扣在土壤中化作肥料,不妨碍下一茬农作物播种耕作和收成。这多省事!希望这好办法早日能在“咱这疙瘩”应用推广,乡亲们就不用再干刨茬子、打茬子这种又脏又累的苦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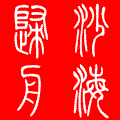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7 14:52:00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8/12/17 14:52:00 [显示全部帖子]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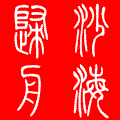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2/18 20:03:00 [显示全部帖子]
Post By:2008/12/18 20:03:00 [显示全部帖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