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丧
陆翀
一
一九七〇年仲春,两狼山脚下,五家河南岸,召圪台村。
麦田刚淌过第一回水,麦苗翠青湛绿。这两年,趁着文革混乱,国家对土地疏于管理之机,近处的耕地沙化了,生产队就带领社员朝远处开垦。一块块形状不规则的麦田,顺着东沙窝的边沿,直伸向远处的枳笈滩。出工劳动的地块,离所居住的村落越来越远了。远的,一趟要走二三十分钟。晌午,我们从河头地蓐谷子回来。男男女女一大群。其中,年轻人居多。一个个扛着锄头,嘻嘻哈哈说笑着,自得其乐地唱着歌。
“走路你走大路,你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儿多,拉个话儿解忧愁。坐船你坐船箱,你不要坐船头。恐怕一个风摆浪,跌得哥哥水里头。……”四后生扯着嗓子,兜着《走西口》。
“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命运唤我奔向远方,奔向远方。我看着世界像沙漠,那四处空旷没人烟。我和任何人都没来往,都没来往,好比星辰迷惘在黑夜当中……”知青小王投入地唱着《拉兹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
“穿林海,过雪原,气冲霄汉……”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
…… ……
古今中外,塞北江南,土调洋腔,美声流行……虽然那么多人同时在自顾自地“独唱”——准确地表达,应当说是在旁若无人地“吼喊”——然而春风骀荡,旷野无垠,天高地阔,兼容并蓄,置身其中,居然不觉得吵闹。蓝天之下,仿佛人们一下子发现了自己声乐的天赋,声嘶力竭地用高亢的歌声,响遏各自头顶上那一圪哒哒白云……
“看——”鬼刘三突然一声大喊,“看——那头前!”
说笑喧哗,顿时煞住;乱唱瞎嚎,戛然而止。顺着鬼刘三的指向,我们远远瞭见西河湾水里面分明是卧着一个人。慌忙跑过去看个究竟。待到近前一看,无不惊愕得倒抽一口凉气——竟然是老魏福!在场的人不禁悚然,唏嘘嗟叹。幸好是空(kong,去声)渠,水不深。但见老魏福头朝下趴在水中,全身浸水湿;瘦长的脖颈一伸一伸挣绷着,三根筋挑着的那颗头,也随着一扬一扬地,像一只干瘦的公鸡,大口大口地喝着空渠里的黄泥汤。他的腰上系着一根麻绳。绳的另一端,栓在渠畔的杨树上。四后生、鬼刘三冲在前面,众人也急忙上前,七手八脚,把他救起。抬到渠背上,空(kong,去声)水。
原来,老魏福企盼着死后热闹风光的事业,实在活得不耐烦了,于是决心跳河寻死。有人说,那天一大早,就瞭见他在沙梁上转悠,可是,没像往常那样挎个箩头,提个粪叉。此话刚一出口,即刻招引出众人七嘴八舌的推理,一下子打破了适才片刻的凄清寂寥。这会儿,不少人又觉见自己颇有大侦探波洛、福尔摩斯那般富于思辩的断案才干了,争先恐后地发表各自的高见——
“老魏福暗中跟老李庚摽劲儿,非要办个大事业给他瞧瞧,让他眼气。可是,老李庚偏偏先他闭了眼!”
“那一阵儿,老魏福沮丧得很,整日价恓恓惶惶,长嘘短叹,愁眉不展。说也怪,人世间,贪生的,定猛死下了;盼死的,却活了一天又一天。老魏福万事俱备,只差下个死了。”
“要不咋听人说,这些天常看见有人大半夜在村口烧纸钱呢,该不是老魏福吧!”
“他选定了约莫该歇晌的时辰,和这人们收工必经的紧靠路边的西河湾,想是怕死下了,人们寻他不见。”
“……系根麻绳,自然是担心被水冲走,办事业没了主角儿。”
“不料想水期已过,河水顶多尺把深。我们跑过去救他时,他还扎挣着,死命趴在水中,一个劲地往肚里灌黄泥汤汤。”
老魏福经这一番折腾,想必是着了凉,当夜就发起烧来。但见他躺在炕上,形容枯槁,气息奄奄;只是深陷在眼窝的两只眼睛,痴痴愣愣地瞪着。兰老婆儿打发女女端来热姜汤;家住本村的于大夫,准备给他打针吃药……他索性谁也不睬,不说不动,拒绝打针,也不肯吃药;惟有痴痴愣愣地瞪着那两只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奕奕有神:分明是在热切地期盼着什么,执着地等待着什么。最后,还是老李会计读懂了他的目光,琢磨透了他的心思。
第二天头晌,老李会计从十几里外的永济渠二闸,寻回了三天前队里派驻到那里去“禁水”(黄灌区水利部门统筹水源分配,淌水时节地处下游的生产队,要派人驻守上游生产队的渠口)的邬三禧、二元仁。看见他俩一进门,老魏福就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头一歪,去了……
原来,邬三禧、二元仁正是老魏福生前早就托咐安顿好了的装裹入殓、杀羊捣糕的人,……
入殓时,老魏福脸上是笑模样。
二
老魏福,老李庚,同是五保户(1),却彼此看不进眼,事事不搁股(2)。老魏福的身量比老李庚高出半头,可是,佝肩驼背,瘦骨嶙峋,不如老李庚硬朗。那张脸,圪蹙得象个干红枣儿。深刻的皱纹上,挂着即使洗也洗不干净的尘垢。论年龄,比李庚差五岁,看脸面,却要老的多。只是深陷在眼眶里的两只眼睛,像两颗土埋尘垢的珍珠,虽说不大一点儿,却矍铄有神。我常见他一天到晚挎个箩头,提个粪叉,漫滩转悠,从不拾闲。
四清时,老魏福是根子户,工作组就住在他家,树他为苦大仇深,爱社如家的典型。老魏福牢记干部们说给他的毛主席语录:“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并由此省悟出自己在村子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影响,走走做做都得有那么个驾套。
那年月,都时兴标榜自己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别人说有,我常置疑。要说老魏福,那可是千真万确,情真意切,我绝对信。每年麦收过后,队上都请老魏福守瓜茅庵。按说,农田地里长出的东西,乡里乡亲,吃上那么两口,算不得过逾。俗话说:“偷瓜摘葫芦,抓住撅不了毬。”老魏福却不然,他是为队上看瓜,对偷瓜的“灰皮”们,他比用铁链子栓在瓜茅庵的黄狗还来得凶。
要说他公正,也不见得。每当开园,老魏福掌秤,给人们分瓜菜时,那秤杆儿一律是往下斜,总怕便宜了社员,让集体吃亏。他心里明白,这样过斤秤,一两一钱地扣卡,脸面上不太好看;可是自己一扑真心,全都为的是给队里赚下点儿。他想,既然是贫下中农当家做主人,就得有主人的心计。要是谁找他理论,他就把脖颈一横,憋红了脸,吵着说:“甚为多来甚为少,甚为喜欢甚为恼?给你就是个好,不给你就是个恼?”劈头盖脸一痛抢白,真能把你噎到南墙去。因他年纪大,脾气倔,又无论亲疏,一律对待,不是专门和谁过不去;差个一两、二两,也就很少有人跟他较真。倒是那串“甚为多来甚为少”的妙论,成了人们开心的噱头。
凭心而论,老魏福对共产党,对新社会,那真是由衷地爱。虽说他身子骨儿不济,挣的工分不多,可省吃俭用,这一个人的日子,过得是应有尽有。玻璃门窗大正房,红漆躺柜满炕毡,大缸小瓮腌菜坛,都置办个齐全。别看他灰蹙蹙地土眉惺眼,也是出门一把锁进门一把火的孤老汉,可家里却收拾的头头是道,窗明几净灶面光,连小油灯都擦的锃亮。不过,有一样,很多值贵的东西,他都舍不得用。比如那个漆着富贵牡丹的铁皮暖壶,从打买回家中,还没沾过一滴水,那是怕上锈呀!四清年间,常搞忆苦思甜的社会调查,村村户户统计添置了多少辆自行车、多少台缝纫机……作为实据,论证新旧社会两重天。老魏福把这些个摆放在明处,当作翻身的明证,幸福的象征,自己看着,心上也舒坦。要是够条件,兴许还要买辆飞鸽车,添台缝纫机什么的,擦得亮亮地,摆到炕头儿上呢。自从五保了,老魏福一门心思筹办着死后的大事业。他想,这可是为贫下中农长脸的事,哪能像西村老李庚那样嗜酒贪杯,满不在乎;光杆儿无聊,要甚没甚,只等人家拆门窗,撤柁檩,抽椽子。
三
那年月,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大小队干部怕戴“当权派”的高帽儿,动不动就脱皮袄,撂扁担,躺倒不干。再加上推行“大寨工”,反正,“干不干,八分半”。人哄地皮,地哄肚皮。这两狼山脚下,五家河南岸的召圪台生产队,尽管开了那么多黑地(瞒着公社,擅自垦荒,不纳农业税的耕地),挤得放牲灵都没草片儿了,可是社员们还得吃返销粮,分红一年不抵一年。“五保户”,吃、穿、住、零花钱全由集体供给。集体要是不景气,“五保户”的收益,顶多维持最低标准;想凭这些进项办事业,难于上青天!老魏福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孤身一人,只靠“五保”;筹办死后的大事业,不异于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绝非易事。
有道是“思想红,万事皆红;穷办法,办法无穷”,老魏福硬是艰苦竭蹶,志在必得。终朝每日,挎个箩头,提个粪叉,漫滩转游着;掏苦菜,割羊草;拾柴禾,捡牛粪;还挖田鼠洞,打弄些麦粒儿、糜谷、豆颗,回来淘洗碾磨了吃。就这样千辛万苦,裤带上挤,牙缝上攒,省下口粮,讨换黄米、麦子、葫油,筹办事业。
喂猪,消耗太大,为精力、物力之所不及。老魏福圈里养着六七只羊,白天托送给队上的羊倌,合群放牧;晚上圈回自家,添草加料。宁可人少吃些,也不能亏待了羊。队干部逢年过节,送来几块钱,他一分钱也舍不得花,全都买下白酒,存起来。到时候办事业,席面上“饮福酒,受胙肉”(3)是少不了的。
别看他平时穿戴破烂,制做下的老衣却是里面三新。棺材早就准备停当了,还油过两遍清漆,亮得能照见人影影。就连到时候,谁个装裹入殓,谁个杀羊捣糕,他也早就托咐安顿个周详。……
偏巧赶上史无前例的岁月,老魏福筹办事业,省吃俭用、费心操劳不说,心上还惊恐万状,备受煎熬——那可真是个“按下葫芦浮起瓢”,“破麻烂糟,实在难熬”。
先是破四旧,红卫兵烧了地富家的棺材、老衣。吓得他吃,吃不踏实;睡,睡不安稳。走着坐着没着落,一天到晚犯嘀咕。多少回刚吹熄灯躺倒下,又爬将起来,倒腾柜底儿藏老衣,扒开柴垛眊棺材;生怕红卫兵半夜来叫门。直到亲见苏后生从部队回家奔丧,军帽上绷了孝,跪在他娘的灵柩前,哀哀祭悼,老魏福才知道,开追悼会就是办事业,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恩准了的。自己家的成分,虽然说探不上什么军属、烈属的,总还是个贫农。可算是长长舒了一口悠悠的气。
没成想转过年,苏后生他爹被打成内人党,造反派扒了他娘的坟,虽说并没从棺材里搜出什么联络图,他还是被部队裁下来,打发回村种地了。老魏福心上又是一咯噔。寻思道,自己什么都准备便宜了,还不如立时死下受用,谁知道往后还要怎么变?
……村口路边有几株胡杨树。树下车来人往的,时间长了便成了一块不小的开阔地。早春天气,乍暖还寒。夜深人静时分,但见满天星斗闪烁,一钩冷月偏西,村子里鸦默雀静,旷野上冷风习习。一个高身量,佝肩驼背,瘦骨嶙峋的老人挎着个箩头,步履蹒跚地走出村口。那正是心中破蔴烂糟,捣挽着睡不着觉的老魏福,为着在“那边”不再受穷,到村路上为自己烧化纸钱。他圪就(蹲)在路当中,伸出干树杈般的手,颤微微的,一边把备在箩头里的纸钱一沓一沓地往火里添续,一边拿根红柳棍,不住往上挑着抖着那些还没有充分燃烧的纸钱。嘴唇歙辟,不知叨念些什么。火焰在风中抖动,火光一闪一闪,映照着他的那张圪蹙得像个干红枣儿的脸。此刻,他那双深陷在眼眶里的眼睛,越发矍铄有神。——毕竟,连日来老魏福已经为自己烧化了足够多的纸钱,可以放心地上路了。这时,一阵旋风卷起纸灰,沿着大道向西盘旋而去……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5:3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5:32:00 [只看该作者]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5:4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5:4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5:5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5:5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6:1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6:12: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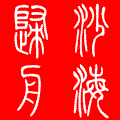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6:1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6:1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6:3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6:3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7:1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7:1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4 19:0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4 19:0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5 18:3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5 18:3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15 22:1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15 22:1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