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历史的深处——《苦难与风流》再版后记
作者:金大陆
《苦难与风流》要再版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选择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十年――接过这个选题,重新审理,全新包装,以使它的内容和意蕴,携带着历史和思想,在跨世纪后,获得新的解读和诠释。
记得那年在绍兴路发行《苦难与风流》,是个闷溽的梅雨天刚刚过去陡然暴热的日子。上午,我去出版社领取样书,巳见有上百人排队了。中午,布置上海老三届作家与读者见面会时,大门外巳围着成千的人群,连公交线路都堵塞了。当晚的电视,第二天的报纸都说"盛况空前",但我作为本书的编者,那天竟然没有一点兴奋。面对鼎沸的场面,一直紧紧地处于忧惧和惊恐之中。我忧惧剧烈摇晃的铁门会倒下来,我惊恐蜂拥的人流中会有人倒下去。后来,不是出版社的老总果敢地翻出墙头,表示敞开全部的库存;不是卢湾区派来一批交警,真不知会不会发生意外的事故。
其实,这是当年上海的老三届人、知青人,借一记载同辈人集体命运的出版物,寄托情思,释放情绪,力图从中寻觅自身的踪影,拨动胸臆间的共鸣(该书一月连印三次,数月位于上海图书销售排行榜前列)。确实也为上海出版史书写了非常的一笔。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老三届人还葆有那么一份倾诉的激情,那么,在本世纪一十年代,起码在统计学意义上说,老三届人大概巳没有这份情致了。不容违碍,这是因为老三届人巳集体性地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不仅仅表现在自然的年岁和职志的位序方面,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新技术、新理念的创造和接受方面。
就此,再版《苦难与风流》的意义何在?!从表面上看,是昔日的打拼变成了今日的赋闲;是昔日的倾诉变成了今日的叨念。从内在里看,却是一个社会学意义的标本,变成了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且时空延展,积淀厚重,即关联着老三届这代人的命运沉浮,恰恰与当代中国的世运向背同频共振,恰恰以"苦难与风流"为主旨写滿了当代中国的史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重新梳理《苦难与风流》,就是要为老三届人及其他们的子女留存一本可供挂怀的读物;就是要为专门家书写当代中国史留存一部可供参阅的文献。
《苦难与风流》注重思想的表达,它有个姊妹篇,是1995年出版的《东方十日谈》,偏重于讲述老三届人的故事;它还有个后继篇,是1998年出版的研究类著作《世运与命运》,着重于探讨老三届人的生存与发展。在该书的第二十七章《生命可贵》中,我记述了"两桩揪心的事":
那就是在笔者所编《苦难与风流》的109位老三届撰稿人中,巳有两位英年早逝了。他们是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吴方和上海复旦大学的朱涌协。
我迄今清晰地记得吴方在电话中矜持又略显沙哑的声音,他起先似乎对该选题的写作有些迟疑,经过探讨和思考后,再次通话时就很沉着地答应了,接着,便寄来一篇独到的文字。吴方是京城很有才华的文学评论家。60年代,他曾背负着出身的包袱经历精神的塑造。70年代,在京西煤矿挖煤时,他曾躺在燕山山野的蔓草丛中,望着飞翔的大雁,任思绪在茫然中捕捉着感觉。以后回城、上学、当编辑、当学者,正当他渐渐地摆脱纠缠,以一颗安详、超脱的平常心去贴近真实的人生时,却被淋巴癌夺去了生命。
我迄今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寒秋的早晨,一位疲惫又略显紧张的中年妇女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她说她是朱涌协的妻子,她说朱涌协患肝病去世了,她说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我给他的一封需要寄回执的信。我像突然掉进了冰窖里,全身的血冻住了,呼吸急促起来。我追问朱涌协的救治情况,她似乎不愿多说;我与她商量可否整理朱涌协的'自学'材料(朱在《苦难与风流》中的文章为《只有自学》),她也显得茫然。我将朱涌协的稿酬翻了倍交给她,嘱她有事可找我,她直直地点头。送她下楼时,望着她沉重的背影消逝在墙角处,我感到胸口很疼痛。
我仰望苍天:这究竟是偶然的降临,还是必然的归趋?
呜呼!老三届的兄弟姐妹,生命承负之重与生命离去之轻为什么如此纠缠在一起?以至在今日的老三届人聚会上,会不时地构成伤感的话题;以至在今日再版《苦难与风流》之际,我要十分悲伤地说,在《苦难与风流》的老三届人作者群中,上海作家陆星儿了巳离我们仙游了。行笔至此,陆星儿诚朴的笑靥一直在我眼前晃动。我要十分伤感地说,《苦难与风流》的责任编辑季永桂先生也巳身患癌症。小季与我中学同学,与我爱人大学同校同届,是熟识的朋友。小季的儿子还小,还未成人,企盼医生无往不宜,妙手回春。相遇改革开放是老三届人的集体幸运,却因种种原因没能顺畅这段路程的老三届人是真正的不幸。但愿这种不幸少一点,小一点;再少一点,再小一点。
关于老三届人的命运研究,既然巳从社会学的框架进入了历史学的视野,它在时间上的追溯将更深远;它在空间上的拓展将更开阔,以及所要面对的史实和问题将更复杂。当下,我任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题从事"上海文革社会史"的写作,"老三届人"仍然是重要的方面,只是现在更注重档案说话,更注重原始史料说话,以求回答和解析老三届人在那个非常时代的种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行动、行为和心态;以求发现和填充那个非常时代的种种尚未进入的空白领域,例如先前研究老三届人上山下乡,多是"战天斗地"和"艰难困苦"的主题,且侧重于面上情况的述说和个人思想的表达,却很少注意主管部门是如何筹谋,基层单位是如何运作,方针政策是如何制定,方案执行是如何变通,以及所有这些情况的来龙去脉等等。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老三届研究还得继续深入下去。
曾听一老三届人说:现在,老三届人的故事儿辈们"不愿听";孙辈们"听不懂",语气里很有嗔怪和不甘的意味。其实,我认为儿辈们"不愿听";孙辈们"听不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当有人"愿意听",当有人"听得懂"的时候,却不知"诉说人"哪儿去了?或者诉说人巳不知"诉说"什么了?我的工作意义在此,价值在此,职责在此。我会在未来的时日里勤奋工作,向广大的关注者、厚爱者奉献出更厚重的成果。
感谢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承载社长的慧眼,正是他的决策和我的意愿一拍即合,才有了这本《苦难与风流》的修订版。然而,恰恰在此时,不能忘记为第一版《苦难与风流》的问世作出贡献的朋友,他们主要是刘久威、丁德富、陈杰、马传荣、鲍淡如、冯克胜、郭栋、杨长征等。
最后,祝老三届朋友们身体健康!
记于2008年7月20日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 16:0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 16:0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 16:1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 16:1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 16:2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 16:2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 18:2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 18:25: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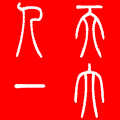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9 10:5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9 10:5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9 11:3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9 11:3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