掸去记忆的灰尘,回想起一九七三年的三月,我们在小脚侦缉队的围追堵截下又回到了东北大地。那些小脚侦缉队可谓用心良苦,手段出奇,夜里十二点查户口,搅的四邻不宁,轮班换人的找家里人做动员工作。让你心神不安,无奈只好打道回府。在京的日子,思维的惯性使自巳仍认为是北京人,可头脑中又总想这是我的家吗?虽然事实无数次的打断这种惯性的梦,可头脑中无数次又把他重新组合,继续着做着那是“北京人”的梦,但梦永远只是梦,梦境打破之后还是要回到现实。
七三年三月南方巳春意盎然,东北依然冰天雪地。记得,11月初我们回北京时下了火车坐上公交车时,北京是绿色满园,可我们却是皮靴皮帽棉大衣。没人不看我们。三月份回东北时,一样不能少,依然受到目送。终于回到了东北吉林我们的第二故乡,东北的春天虽然也巳经有了一点迹像,那不过是从零下二十度升到零下十度。在那个年代东北农村的冬天,是人们坐在热炕头,抽着卷大炮,喝着浓浓的红茶,整天吹牛的日子。(那年头没有麻将牌,如果有,嘿!麻将声肯定响彻东北)而我们从北京带回的兴奋,随着从北京带回的吃的东西减少也同样的减少,直至消失的无踪无影。
每天的无所事事,我们竟然想出了比懒的主意,冠军是小山子,七天七夜,除了方便外均在被窝里。到第七天他起来时得扶着墙才能站稳,适应了好一会擅抖着走出第一步。这天有人提出串户,立刻得到响应。附近一天打来回路程的,巳提不起精神来了,因此决定到三十里外,另一个公社的集体户去。几个人立刻兴奋起来,商量半天决定明天早出发,估计吃中午饭时能到。一夜无话,到早上天刚亮,我就起来冼漱完毕,一看这三个家伙还没睁眼呢。马上叫他们,没有人理我的,嘿!不起,拽起来,拖这个坐起来了再去拖那个,那个还没拖起来呢,这个又钻被窝里了。气的我干瞪眼,只好做罢。直到九点他们才起身,打着哈欠问我做饭没,我说没做,他们立刻瞪圆了眼晴,吼道:都几点了,还想不想去了。气的我抄起笤帚向他们打去,叫你们早起谁都不动,他们三个嘻嘻哈哈的跳着躲着都去刷牙洗脸去了。乘着他们洗漱的空,用烧好的水熬点棒子面粥,胡乱吃了几口,就出门上路了。
出得门来,只见明日当头,懒洋洋的向雪原上播撒着他那微弱的热能。虽然风不大可吹在脸上也像刀子一样刺的脸皮生痛,也许是刚出来的原因,过一会就适应了,虽然风仍在吹,感觉好多了。踏上去“小陈”他们所在屯子(村子)的路,哥们几个一挥手吼了一声前进,就开始了艰难的旅程。说是路其实就是车,马,人踩出来的,也只能勉强称之为路。四人有说有笑的走着聊着,大约一点右左,天边突然出现一股云团,这时小风不知何时停了,四周一片寂静。我们看了一会,没理会,继续走。
不一会那股云团来到眼前,刹那间狂风呼号漫天飞雪,太阳依然高挂,却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几个一惊,知道遇上当地人称之为“大烟泡”的暴风雪了。就是大风把地上的浮雪吹起迷漫在空中,密度很大,像浓雾一样,对于出门在外的人非常可怕,一,温度聚降,二,风雪中极易迷路,在我们插队的地方,近的屯子(村)相距七八里路,远的一二十里。如果迷路了,生死难料。现在回去己不可能了,因为在大烟泡里前进后退都是一样的。只有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四人只好手拉着手艰难的向前走着,这时风巳经把雪地刮平了根本看不到路。我们加快步伐,盼望着尽快的冲出暴风雪,可这也只是我们一厢情愿,因为大烟泡一起,小则几十里大则几百里,何谈冲出。只是徒费气力而巳,也算加快了速度。但是这也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走着走着,眼前慕然出现一道黑影,伸手一摸,原来是道墙,几个人心中一喜,有墙就有房、有房、就有人家。赶忙摸着墙想找到门。可让我们心凉的是,这是个破方框子。(东北有一种盖房子的方法叫“干打垒”就是用拌合土用木棰一层层打起来,整个房子的墙是一个整体。冬暖夏凉,但养护麻烦)就是干打垒的临时用房,走时把房梁拽下来,只剩下墙称为破方框子。几个人走了进去由于墙挡住风雪,风明显弱了许多,得以喘息的机会。
喘息稍定,张建京抬头问了一句:“你们记得路上有这个方框子吗?”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但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都冒出三个想都不愿想的字“迷路了”在狂风呼号中不知过多久,又是张建京,抬起头来,说出了一个字;‘走’。我们三个异口同声:“你疯了,等风小点再走嘛”。张建京坚定的说:“必须走,一、日落北风刹那时天巳黑了,二、我们巳经迷路了,在这呆着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无论如何,只有走才有可能有活路”。这时我们才明白过来,死神巳悄然跟在我们身后了。一咬牙,又闯进了暴风雪。
不知走了多久,风渐渐的小了,可天色也渐渐的黑了下来。这时隐约看到前面的有道河,几个人兴奋的向前狂奔。因为同学的屯子在河对岸700米处。到河边就等于找到了屯子,找到了屯子就找到了集体户。可等到了河边向对岸望去一片雪原,那里有屯子呀。我们几个一屁股坐在雪地上。现实情况是迷路了,同学集体户所在的屯子不知在东还是在西。如果向东找而屯子在西边,其后果是:向东二十几里是嫩江过了江就是黑龙江省,不会有人家。向西也不好说能找到人家。
几个人坐在雪地里,都默不作声,不知如何是好。可老天并没有因我们停顿而停住他那拉上天空黑幕的手。还是张建京抬起头说了一句;“咱们“猜嘣吧”(硬币),正面向东走,背面向西走”。见我们没反对,从口袋里搜了一会,找出一枚硬币。说了句我抛了,说着抛出了那枚决定我们命运的硬币,可是这毕竟是决定命运的,他也紧张,以致他的手也不由自主擅抖起来,竟然没接住,只好从雪里抠出来重抛,这次接住了。随着他手指缓缓张开,四双眼晴紧张的看着,待手指全张开,看到那枚硬币是正面。
这时天色已渐渐的黑了下来,别废话,过河。过了河就向东走,我们有意识的偏离河边约300米右左。因为屯子离河边约六七百米,偏离河边300米,即可沿着河边走不会迷路,又可发现300米外的屯子。想法是好的,如果是在白天无疑是正确的,可惜,已经太晚了,走着走着天完全黑了下来。这时饥饿又使我们脚步更加沉重。要知道在雪地里走路,趟雪走累,可抬脚走更累,从风雪开始时,风吹起的雪巳把本来就小的可怜的路复盖了。就巳经没路了。原本小路的雪被车马把雪压实了还好走一点,可现在只有趟雪走了。我们四人艰难的向前走着,谁也不说话。天空只有窄窄月牙发出惨淡微光,根本不起做用。而星光虽然灿烂可对我们来说一点帮助也没有。能见度只有几十米。死神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向前走不知前面等着我们的是什么,而停下来却只有一个结果。
又向前走了一会,小芦停下了脚步,向右前方一指说你们看那是什么,我们三人瞪大眼睛向他手指的方向看了一会,什么也没有呀!问他你看到了什么,他说好像有点亮的东西。我们又看了看还是什么都没有,不知谁问了一句是不是鬼火,他也说不清楚,我们停了下来,。我们再一次问他你看见的是什么,他也还是说不清。于是我们决定向他所指的方向走,走了约几十米,看见了极弱的一点亮光,四个人立即兴奋了起来,忘记了身上的疲劳,忘记了腹中的饥饿,向那亮光加快速度走去。越来越清楚了,那是一扇窗户发出的灯光。
我们四人相拥而泣,我们巳把死神赶走了。看到灯光就有屯子,有了屯子就安全了。顺着灯光向前找到了进屯子的路,又找到了集体户。谢天,谢地,谢谢岳元帅。赶紧上前敲门,门开了小陈看到了我们,大吃一惊。你们怎么来的,我们异口同声的说:“别废话了,赶紧拿吃的,晚一会哥们四个一个你也见不着了”小陈说:“怎么回事”,嗨,这都不明白,饿死了呗,小陈气的说你们还是不饿,有斗嘴的功夫早都吃上了。
他们集体户的人,有拿大贴饼子的,有拿咸菜的,有拿碗倒开水的,一时间小炕桌上也摆的挺满的。我们正脱衣服时闻到一股非常熟悉的昧道,顺着这股昧道定晴看去,哈!北京臭豆腐。够奢侈的,我们从北京带那些吃的,早就进五谷轮回之所了,看来人家日子过的细。赶忙把衣物甩掉,脱了鞋就窜上了炕,狼吞虎咽的吃上了。小陈说:知道你们饿了也就没熬粥,贴饼子也不算凉,就着开水凑和吃吧,没人理他,只顾吃了,气的他说:瞧你们那吃相,是饿死鬼托生的,他们户的那哥们几个坐一边看我们直乐。现在还顾的上吃相,才不管他哩,那贴饼子就臭豆腐的滋味终生难忘,就现在还惦记这口哪。
吃了半饱时有点气力了,才把路上所经历如实的讲述了一遍。小陈楞了一会,才说:“你们胆也忒大了,“猜嘣”,亏你们想的出来,如果是背面哪?往西奔那去了,你们知道吗?顺着河走就奔黑鱼泡了(当地人把湖泊称之为‘泡’),中国地图上都看的见,方圆几十公里没人家。”这时四个正低头喝水的脑袋同时抬起来,张大嘴吧,共同发出了一个字“啊”。
前面找到集体户后所说:“谢天,谢地,谢谢岳元帅”谢天,谢地为口头语,可谢岳元帅,只有我解释,您才清楚。我们插队的地方原来为满,蒙两族杂居的地域,后来汉族人也来到这里,因为这里地多,所以一人带二人,二人带四人的称为闯关东。逐渐成为汉,蒙,满三族人杂居的地区,再后来汉人移居此地的人逐渐的多了,满族人就向北迁移了,剩下为数不多的满族人散居在各屯子里,有的屯子只有一户,有的屯子还没有。
蒙汉两族人家,都不留西窗户,因为当地冬天长,常年刮西北风,所以为了保暖,只是南面留窗户。如果这样我们就不可能看到灯光了。可恰巧小陈他们户所在的屯子里有这么一户满族人家,恰巧他们家西窗户的灯光被小芦发现了。我们才找到屯子,找到了集体户。
八月十五吃月饼的典故想必大家都知道,而当地满族人认为他们的祖先就是八月十五那天从西窗户逃出来的,而更多的满人被杀了。所以当地的满族人都习惯居住在屯子西边,而且都留西窗户。当地满族人习俗是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不吃饭,到天黑后捧着一个黄包袱,全家老小到家里西窗下祭拜,所以才有我们谢谢岳元帅一说。虽然这一切不过是传说,但当地满族人家都留西窗却是事实。
2007.6.20 苍狼向月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0 13:5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0 13:5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0 17:0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0 17:0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0 19:3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0 19:3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0 21:4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0 21:4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1 8:2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1 8:2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1 9:0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1 9:0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1 15:4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1 15:43: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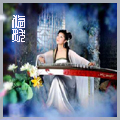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1 18:1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1 18:1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1 20:0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1 20:0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22 9:3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22 9:31: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