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个夏天的彩虹(6)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洛塔那边也没有任何凌云的消息传来。
一个月过去了。
两个月过去了。
就好像她从未来过这儿一样,我没听到任何人谈到过有关她的消息。我越来越焦急,在单位里偶尔见到一两个从洛塔上来办事的人,我忍不住要多看他一眼,仿佛他的脸上能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我柰不住了,我想给她写封信,但寄到哪儿去呢?她不会一直在洛塔的,她会到处跑。她是不是出什么事了?这里没人认识她,即使她从此销声匿迹。整个丽江除了我,谁还能去寻找她?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不行,我得找她。我接连挂了几个电话,给那些在下面乡镇工作的老同学、熟人打听凌云的消息。一无所获,只有宁蒗的人说,曾在街上见到一位女同志拿着像机照相。我不能判断那是不是她。咳,我该怎么办?偌大的丽江地区,谁知道她躲在哪座山?哪条沟?我只能在沉默中守候着她的信息。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快到下班时间了,电话响起来,我拿起话筒。“喂,请找一下莫存友”。传来一个甜美动听的女声。“凌云!”我惊喜得差点跳起来。
“喂,是老莫吗?你好”。 她的声音平静略带笑意。
“我的天哪!你到哪儿去了?”
“怎么,出什么事了吗?”她疑惑问。
“出什么事?你快把人急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电话?” 我不由得怪起她来。
“噢”。她轻笑。“有很久了吗?就两个月嘛,你担心什么?”
“我……咳,我怕狼把你叼走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说了一句很傻的话。
“啊呵呵呵”。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问。
“我在高原宾馆,今天刚从泸沽湖那边回来”。
“我这就来”。我放下电话,骑上脚踏车,直奔高原宾馆。我一步三个台阶地走上楼去,上面却有个人在下楼,走到照面,我抬头一看,原来这就是凌云,她来迎我。她向我伸出右手,“老莫,给你添了不少麻烦,真不好意思”。 我握了握她的手,她的手瘦小而有力。她的目光在温和中又增添了几分热切。她的头发长长了,两个月来,她是没有地方可去修理头发的。为了束过长的头发,她在头顶戴了一个格子布做的发卡,使她简洁、朴素的学者形象上添了几分淑丽。身上穿着一件浅蓝色布衬衫,脚蹬拖鞋。大约是刚洗浴过吧,她的头发有点湿,周身散发着一股香气。
“这么长时间,你在哪里住?” 我问。
“我到处跑,跑到哪儿就住到哪儿,有时到一个较大的寨子里,我就住上几天。上个月我主要在永宁地区”。
“每天就吃一包饼干吗?”
她笑起来,“到哪里去买饼干吃?我住在哪家就在哪家吃,人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这很简单”。
“叫我过两个月这样的生活我恐怕受不了”。
“那当然,你是坐办公室的秀才老爷。干我们这行的不同哟”。她那弯弯的明媚的眼睛仍含着笑意,话语也总温和平静,我从未见过她大惊小怪地夸张什么,或责怪什么。
我们走进她住的房间,她指着沙发说:“请坐”。床上摊放着许多东西。一个像机,几件叠好的衣服,两个厚厚的笔记本。还有小镜子、梳子等等。她说:“很乱是吧?我正在收拾东西”。我看见那堆杂物里有一个长长的木牌,一头是尖尖的,宽的那一头画满了奇奇怪怪的东西,就走过去把它拿在手里说:“这是干什么用的?”
“哦,这是东巴教祭祀使用的法器”。
“连我这个土著都没见过这东西,我一点都不懂,你从什么地方找到的?”
“一个老祭司给我的。他就住在离丽江城很近的地方”。
未完
。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4 21:3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4 21:3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4 21:5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4 21:5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4 21:5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4 21:5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4 21:5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4 21:5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5 8:0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5 8:00: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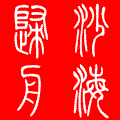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5 9: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5 9: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6/26 11:1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6/26 11:10: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