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恋自然就是当年知青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知青刚到农村那会,大都不到二十,因此也显得比较单纯和幼稚,因而在个人的情感方面亦无过多的烦恼。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年龄的增长,单调的乡村生活和年轻人青春生理所带来的某种特有变化,开始日益变得强烈。尤其对那些感情相对丰富、或者说是缺少某种克制力的知青来说,他们似乎开始比常人提早进入恋爱和结婚的阶段。
这种情况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也有着重要的环境因素,当然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生理特点、家庭情况和认知亦密切相关。既有生活和环境所迫,也有青春生理所需,更不乏仅是作为一种排解心理空虚的游戏。由于年轻幼稚、生活贫困、甚至缺少心理准备,因而,对大多数知青来说,这种恋爱和结婚或许少了些许甜蜜,却多了几分烦恼和苦涩。
当然任何社会或每个年代都有各种版本婚恋失败的众多故事,也不乏劳燕分飞,甚至恋人成仇、夫妻成敌,或婚后生活穷困潦倒的诸多现象。但是,因社会因素造成那些现象的,大概在那一特殊年代的知青身上反映得更为强烈、更为凄楚。当然,知青恋爱婚姻中也不乏真正两情相悦、相濡以沫、同甘共苦者,以及因此而培育并结出真挚爱情硕果的幸福伉俪。然而,无论如何,知青们所经历的这条人生之路,远比如今的青年来得艰难、来得痛苦,甚至来得凄婉。
应该说,最初两年我们这些大多数似乎还是毛孩子的知青,对恋爱婚姻的认知几乎是很苍白的。因为一则年事小了点,二则当时我们的知青点基本还是沿袭着上海中学中男女生界限分明、互不搭理的做法。以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多数男女知青仍互不搭话。
再说,那时节的年轻人由于更多地接受了传统的红色革命教育,因而对人们赖以繁衍生息的恋爱和婚姻的理解也是极为幼稚的,对“性”的字眼也是讳莫如深的,当然对其的认知肯定也是错误的,甚至是无知和茫然的。即使后几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对异性好感的产生,大多数人还不敢轻举妄动。其原因,除了受到思想观念方面的束缚外,还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所带来的各种困惑。
困惑既包括不甘长期呆在农村、指望上学或招工的期盼,也有无法适应盖房、生子、终日劳作田间的农村长期生活的想象。于是,压抑自己的情感,或是说放弃青春时期应该得到的那种美好追求,便是我们当时极为普遍、也是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毫无疑问,我们那代人,绝无当今年轻人那般的开放和浪漫,更不可能有如今“想唱就唱、想爱就爱”的快乐境界。尤其是在我们新立大队所谓“正人君子”扎堆的地方,更是缺少那种自然条件和土壤。早恋的现象即便有,头两年也是处于藏着掖着的状态,一般不会大模大样。
即使到了后几年,新立知青相互间恋爱的也不多。有的话也无其他有些队那样整天成双成对,甚至有些“肆无忌惮”的模样。以至于某天清早,一位起早到井台边挑水的男生,偶尔间见到两位恋人在食堂亲热的情景时,不由惊异得如同发现天外来客那般,赶紧扔下水桶,迅即奔跑到宿舍将这一当时我们看来有些吃惊的举动、甚至似乎是特大快讯,告诉给还未从梦中醒来的我们。
我也非常清楚地记得,1973年初夏的一个夜晚,在我们知青宿舍借宿的上海慰问团干部有些惊讶地对我们说,你们队里的知青晚上怎么都呆在宿舍中?而在其他队里夜晚的宿舍中是基本没人的,往往只剩下我们几个老头子,男女知青大都成双成对地出外谈情说爱去了。
诚然,婚姻实质上是一种自然法则,本该是无可厚非的东西。但是,当时许多人的婚姻似乎多了一份悲情。知青与当地青年的结合,是当时涉及面较广、酿成苦果最多的一种婚姻。在知青与当地青年结合的婚姻中,女知青嫁给当地男青年的人数明显超过了男知青娶当地女青年的人数。这因为,一般来说,女知青的体格、群体意识和与艰苦环境的抗争能力要逊色于男知青。在远离家人和面对艰苦的劳动时,女知青更需要得到别人的爱抚、友情、关心和帮助,尤其是当下乡初的热情冷却、幻想破灭时,她们很容易为当地男青年的慷慨帮助所打动,成为婚姻的俘虏。她们往往会用一种实质上是非常沉重的代价,去换取不用下地干活或所谓的安安稳稳在家过日子的生活。
印象中,我们公社知青最早结婚的是五三大队的一位女生,她嫁给了当地一位老乡。这是我们刚到农村的第二年,尽管女青年已到当时法定的结婚年龄十八岁,但仍让我们那些上海知青感到非常吃惊,尤其是听人说那长相不错的女知青,竟然嫁给一个家中穷得叮当响、甚至有些“二癞子”的人时,更觉得不可思议。那消息当时绝对是一条爆炸性新闻,瞬间便在各知青点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没多久,我们的筑路营驻扎在松树沟,于是,满怀好奇心的我们,便偷偷来到他们的“新房”外试图探个究竟。意想不到的是,所谓“新房”竟无半点新房的模样,不过是一间外墙斑斑驳驳很破旧的泥草房,透过窗户看到的除了一铺土炕外,竟无任何家具,实实足足一副家徒四壁的惨象。当时我们着实抽了一口冷气,实在想不通那女生为什么如此急着走上那条婚嫁之路,为什么那么义无反顾地过上那种非常贫困且有些遭人白眼的艰难生活?
个中的原因大概只有那两位当事人最明白,旁人似乎也没有太多关注和责备的理由,不过长久以来一直感到有些百思不得其解。欣慰的是,不久前,听说那两位当事人以后日子过得不错,两个子女也都蛮有出息,全家也都回到了上海,过上了平安稳定的生活。
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多年后,本人竟然在同队的知青家中见到了当初那件事情的男主角——那位曾经的当地青年。令人有些吃惊的是,此人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似乎是个极善侃的人。我不禁暗暗思忖,难道当初竟是那张三寸不烂之舌打动了女孩的芳心,抑或还有其他原因?其实,无论是“是”或是“不是”,都已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过得很好也许是最好的答案。
也就是在我们到农村的两三年后,知青结婚的消息开始不断传入我们的耳中。不过,这类消息的女主角大都是上海知青。一般而言,女知青嫁给当地男青年要省去许多对知青来说非常难办的盖房等事情,这或许也是为什么男知青很少在当地结婚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些女知青离开知青集体户,便开始了一种新的、也许是更陌生的生活,那种滋味和体会也只有她们最清楚,我们是绝无法揣摸的。但无论如何,她们好歹也算有了一个家,也多了一份依靠,或许还多了一份似乎并不美妙的希冀。
就是在那个时节,我们的知青点也出现了首个结婚户,女知青小顾嫁给了当地的男青年栾昌友。小顾年长我们几岁,身材矮小的她很难适应黑龙江农村繁重的农活,或许她非常需要尽早摆脱那种生活的羁绊,因此她的出嫁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她也因此比我们大多数的知青更早地进入了一种新的、在她看来似乎是较好、但肯定是并不太美好的生活状态。或许那种状态会长期地影响着她的整个人生。
小顾的结婚仪式无疑是简朴的,在那个年代、那块地方、那种场合,你想奢侈和排场也绝无可能。尽管没有花轿,没有更多的嫁妆,但必须要有因地制宜、也算比较隆重的嫁娶仪式。
于是胶轮马车替代了花轿,辕马和套马辔头上结上的红绸替代了婚车上的鲜花和彩带。尽管知青宿舍与她们的新房近在咫尺,但是穿着一身新装的新郎还是拉上新娘,并带上陪伴的傧相和小顾的几个小姐妹,坐着马车,打着响鞭,欢欢喜喜地在屯子里转悠了一番。
那时,只听得阵阵马蹄声和串串欢笑声荡漾在宁静的屯中,只觉得本该充满甜蜜和幸福的欢声笑语中,似乎多了几分难以言状的东西,这东西究竟是什么?一时也很难界定。我们曾见过无数的婚车,见过不少的婚礼,但似乎唯有小顾的结婚仪式留下的印象最深。
也许是知青们对同伴的这种变化还不太适应,不少知青对小顾的终生大事的态度似乎表现得格外淡定,除了一些比较要好的女知青帮着张罗一番、一部分知青送了些薄礼及喝了顿在我们看来非常简单的喜酒外,许多知青更多地是作为一位旁观者,而没有给予其更多的支持,哪怕是形式上的某种呼应。或许,那时节小顾很需要这种支持,哪怕仅仅是精神上的某种慰藉。但是,我们这些压根还未长大的学生似乎连在道义上也未给小顾任何赠与,今天看来,或许这正是当时我们的幼稚之处!
应该说,恋爱和婚姻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两情相悦的感情升华、男女之间肌肤相亲的精神享受、人性固有的天伦之乐。然而,在那个特殊年代,知青们在经历那一过程时,与如今年轻人相比,缺少了许多欢乐。所面对的,更多的却是悲情和痛苦,至少是多了不少难以想象的烦恼和忧愁。
著名作家叶辛的小说《孽债》,很好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知青恋爱婚姻所引起的思想冲突、社会矛盾和家庭悲剧。尽管大多数知青的经历,不可能都如该小说描述的那般曲折,矛盾也未必如其中所反映的那样尖锐,但那份磨难和辛酸几乎是如出一辙和无法避开的。
尤其是对于那些选择农村青年作为配偶的上海知青来说,不知是世俗观念作祟,还是城里人的偏见,或是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们所遭遇的艰辛与磨难,似乎远比同为知青组成的家庭多得多,他们遭受的心灵上的痛苦和生活中的困难也似乎比后者多得多,他们的生活旅程大都比常人走得更为艰辛。
知青作家贾宏图在他的小说《我们的故事中》曾讲述了一个发生在逊克的真实故事(见附文),其男主人公戴剑馘是小说《拉幕吧,戏演完了》的作者,本人也曾与之打过交道。故事情节十分凄美,也非常感人。自然,大多与当地青年成婚的知青的婚姻不会如该故事主人公那样曲折和凄楚,也不一定有那样的喜剧结果,但他们的遭遇和经历却似乎同样令人唏嘘、同样耐人寻味。
在那时,与当地青年结婚的知青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巨大压力。因为几乎所有的父母对子女违背自己的意愿在农村贸然“扎根”都不会泰然处之,于是许多知青不得不面对断绝经济资助、或以中断家庭关系为要挟等,那些最常见的压力或手段。为了维护那份感情或者说是婚姻,他们需要承受许许多多的压力,其中包括回城探亲时来自亲友、邻居、老同学们的冷嘲热讽。因而,使得本该非常快活的人生重要一步,却走得非常不爽,以至于长时间一直与忧心忡忡相伴,被一层厚厚且挥之不去的阴影所笼罩。
当然,更感到痛心的是,因为与农村青年成婚,作为上海知青的一方,往往不能与大多的知青一起返城,一般会稍后几年回沪,以至于使他们很难较快融入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上海,很难适应本来节奏就显得非常之快的上海城市生活,很难有一份较为称心的工作,因而生活也就过得相对较为艰辛。因为与农村青年相恋和成婚,作为上海知青的一方,在子女入户等问题上多了几分阻力和烦恼,甚至会为兄弟姊妹所设置的障碍搞得心力交瘁,原先兄弟姊妹的关系也会因此而变得形同陌路。因为与农村青年相恋和成婚,他们多了许许多多本该不应有的曲折,多了许许多多远甚于常人的忧愁和烦恼。
同样,正如《孽债》所揭露的那个年代因知青返城而引发的许许多多悲欢离合的故事那样,大规模的知青返城,也给一些知青那份原本并不太坚固的恋爱带来了考验。虽然新立的知青没有留下如叶辛笔下的那份孽债,但也发生了一些当初看起来似乎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回到上海,回到那个受到西方思想文化长期浸润、曾经名震全球的十里洋场,来到远比新立屯广阔得多得多的更大天地,人们似乎有了一次重新洗牌的机会,处于婚龄的年轻人也就多了几分重新选择的理由。于是,有些已相处得很好、甚至本该进入婚嫁程序的恋人,不得不因某一方的情变而就此分手。
因为一方回到上海,而某一方一时未能回到上海,人们不得不面对日后两地分居所带来的不便和尴尬,“目光长远”且非常现实地选择了放弃。放弃了那份原本非常纯真的感情,放弃了那份因曾经同甘共苦而得到的真挚,放弃了那份当初曾让我们羡慕不已的初恋。尽管我们无意担当“从一而终”腐朽观念的卫道士,不过,当初、甚至今天,我也经常会庸人自扰地胡思乱想,经常会为那些曾经情投意合而最后分手的插兄插妹感到惋惜、感到痛心。
其实,婚姻这档子事情,也正如作家池莉所说的那样“离婚不是件坏事,是一件正常的事,……婚姻就是一个契约,和世上所有的合作都一样,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恋爱不过就是一种意向,有了意向只不过表示有一种进一步发展的可能,并不能保证一定成功,何况经济社会生活中签过意向书而最后不成功的事实也是实在太多。因此,尽管我们对插兄插妹的分手感到惋惜和痛心,但大可不必对此加以指摘,或者不负责任地说三道四。
显然,放弃有很多种理由,那种理由也许只有当事人自己更加明白。使人宽慰的是,那些分手的兄妹们现今生活大都过得很好。这是缘分不够的关系?抑或是时间是抹平心灵创伤的最好东西所致?这辈子我们大概是永远弄不明白,或许也是不需要我们去弄明白的。
在农村接受再教育时,女知青嫁给男知青的很少,因为男知青负担不起家庭的重任。更多的是因为前途未卜,而斩断情丝······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2 15: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2 15: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2 16:1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2 16:1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2 20:2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2 20:2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2 20:4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2 20:4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2 23: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2 23: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3 11:0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3 11:03: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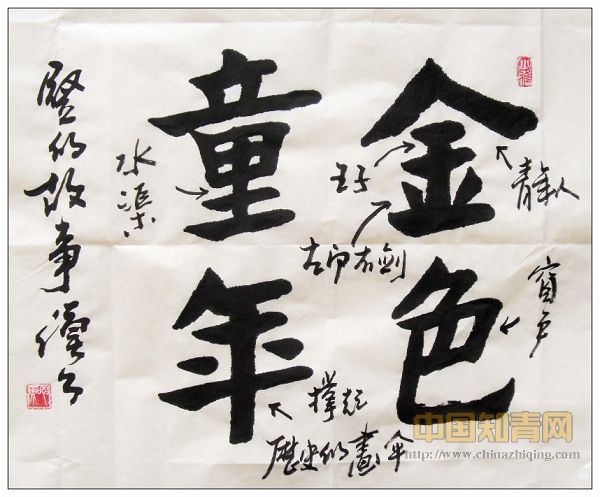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3 13:1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3 13:1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4 13:4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4 13:4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5 9:3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5 9:3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0/8/11 23:0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0/8/11 23:0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