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胡琴缘
作者:英铭
人总会做梦,有的梦是过眼烟云,有的梦则是一生的追求,也是一生不能舍弃的。然而这个美梦屡屡遭遇坎坷或者挫败的时候,美梦便成了支离破碎的、断断续续记忆。梦还会延续,甚至还想竭尽全力把那些碎片拼凑在一起,但终因时间的推移,梦也就变成了淡淡的回忆。这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尘封已久的美梦再次浮现,这种做梦的欲望便被瞬间点燃,梦想成真变成了最大化的渴求。这种渴求达到一种极至的时候,人就变成了一个疯子。疯子是没有理性的,也是自由的,乐此不疲到处碰撞。乱撞的疯子幸运地遇到了仙人,仙人耐心地比划着,指着前面说,梦可以继续,你在路上!疯子安静了,清醒了,也看到了路标。疯子语塞了,眼睛湿润了,似乎想说什么,好像也在喃喃自语,但言词和文字的力量显得无比的苍白。看似一个故事却没有主人公。好像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疯子,说了一顿却语无伦次。一个真实的故事。
上小学的时候正值中国文革后期的莺歌燕舞,我便与二胡结缘。老师让我们用空弦到简单的手指压弦从《东方红》学起,认识了胡琴。我的老师也能拉几首简单的曲子。邻村的学校有一位不错的老师,我每次走几里路也只能是去看看老师拉一两个曲子。学校的胡琴不能拿回家里,只能在学校练习。自己就用铁的圆罐头瓶子做了琴筒,把三合板剥离一层用胶水占到铁筒上。趁饲养员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在生产队的马的马尾上拽下一些马尾,撇下村里住着解放军用的竹子扫帚上的竹棍,绑上马尾制成了琴弓。就这样用自己制作的胡琴拉。家里的大人反对我学习胡琴,说那是下三滥的事情,并说要折断我的胡琴。我每天只能在放学后大人还没有回家的这段时间拉一会儿,大人回来了我就把胡琴放到柴堆里藏起来。等我能够拉成个调子了,大人也不太反对了,我就有制作了一把羊皮二胡,琴弓仍然是原来的马尾竹棍。后来就被招到了公社宣传队,宣传队里有个北京“老知”拉琴拉的很好,从“老知”那里断断续续听会了《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那时很想拜“老知”为师,人家看我一个小孩子也不怎么理会,我就跟妈妈说了,想请“老知”到家里吃饭拜师。老师答应了。那时家里很穷,一家六口人连饭都吃不饱,村里分的口粮都不够吃,家里的成分又是地主,过年生产队直接给六元钱过年。好不容易说服了妈妈答应请老师吃饭,妈妈把家里仅有的白面蒸了包子,做了几个菜等老师吃饭。我们做好饭等了一天,老师没来。妈妈把我打了一顿(过年的白面都蒸了包子)我的二胡也被妈妈折断了......邻村的那个老师教的一个学生(我们宣传队的好朋友)我还是不死心,每天走好几里去听,老师教,那个朋友拉,我只能在一边看,听会了《奔驰在千里草原》。上高中了,我仍然没心思读书,别人上自习我就去当地的“八音会”去听。一次趁人家休息的间隙,我忍不住拿起了二胡,胡琴刚响,就被人家奚落了一顿。从此我便不再拉胡琴了。上大学后有的同学拿着二胡拉,我有时候也拉两下。参加工作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把二胡,但是为了生计,拉的也很少。偶尔看到和听到了二胡的声音就情不自禁,有时候看到有的老师啦的很好,想教一下,总是被不屑一顾的眼神刺的我欲言又止。自己也感觉水平太低,现在学习也晚了。儿子小时候我想让他学习二胡,找了最好的老师,结老师却让自己的妹妹教学生,连示范都很少,我借孩子请教老师的时候,总是以模糊的言语搪塞,而孩子对二胡也没什么兴趣。就这样我彻底放下了二胡梦。但在网络世界深入生活的今天,我还是忍不住地有时候去听听二胡曲。也是偶然的机会我来到了二胡世界网和中国二话房间,看到了那么多中老年人在学习二胡,我又心动了。但自己的二胡也不知去向了。
有一天同事的孩子拿着二胡去了单位(孩子要去学琴),我看着二胡收就痒,拿起来拉了两段,同事说你的二胡拉的这么好,你一定经常拉吧,我说至少有10年没动过二胡了,他说你应该买一把二胡好好拉,我当即就去商店买了一把二胡。晚上就在二胡房间听,在网络上听二胡曲,看一些名家老师示范,只凭自己的感觉去拉,总觉得不能有什么突破,但自己感觉还不错。每每通过二胡房间请教有的老师问题的时候,也还是我前面遇到的情况,有的默默无语,有的哼哈少言,有的讲点大道理,有的始终无应答。但我已经决定好好学习,以弥补我一生二胡梦的缺憾。我终于遇到了一位老师,她的耐心,她的真诚让我感动、让我心颤、让我重新做起了二胡的美梦。一个一生酷爱二胡的人在经历了许多坎坷之后得到了您无私的教诲和指导,那种感激,唉!不说了,最后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您,敬爱的奇缘哆老师,香枝丽燕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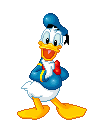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0/28 9:1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0/28 9:1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0/28 16:2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0/28 16:2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10/28 16:2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10/28 16:2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