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中国,无雪的冬天
——我的1977高考
1977年10月,我正在黄山参加一个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一天早晨,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连播中获悉,党中央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我们非常兴奋-----为春天终于叩响冰封的中国的门窗,为我们已经被耽误的这一代人将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急忙赶回芜湖,和朋友们商量怎么去报考,大家都很兴奋,准备跃跃欲试。在仓促中我们重新拾起已经荒废了十多年的高中课本,一切从头来。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把主要精力放在复习数学上,背那么多的公式与定理,演算了大量的习题。时间太紧迫了,从报名到考试仅仅只有一个多月时间,我每天只睡4个小时,很少有这样旺盛的精力。考试时间安排在12月中旬,这是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高考。1977年的冬天是一个暖冬,没有下雪,虽然镜湖结了一层薄冰,但是,聚集在考场外的5000多名考生却如沫春风,竟然没有感到一点寒意。文科考场就设在我的母校-----芜湖三中,我的座位竟然是我读高三时的教室,历史和我们开了一个残酷的大玩笑!由于我是老高三,文化基础扎实,所以各门课程考试的感觉良好。果然在1978年元旦后,我就收到招生体检的通知,在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这些参加体检的人,相互高兴地打招呼,好像一只脚已经跨进大学的大门似的。
1978年春节以后,不少人陆续收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他们兴奋得跳起来。而我望眼欲穿“千帆过尽皆不是”,我知道这决不是考试成绩的原因,肯定依旧是家庭出身问题。因为我的父母都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为此,多年来我一直受到株连。市招生办工作的刘延业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可怕的家庭出身问题,,我所在单位的主管部门--------芜湖市手工业局在我的档案上签了“不予录取”的意见。虽然我的考试成绩是317分的高分(那年高考成绩的满分是400分),我的考生档案一直锁在市招生办的铁柜里。
我愤怒了!春天已经来到中国,为什么春风就吹不到我的身上?我勇敢地去找主管部门的头头评理,我站在芜湖市委办公室外,等候正在开会的市委副书记程介一出来上厕所,向他递交我的申诉信,我慷慨激昂地给当时担任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同志上书,向他倾诉我心中的愤懑-----
正在我心灰意冷,在焦灼却不抱多大希望的期盼中,命运有了转机;在中共安徽省委领导的干预下(分管文教的省委副书记赵守一在我们的上书信上作了重要批示),芜湖市16位因受家庭问题株连的考生被补录到一所师范学院,终于挤上最后一班车。报到的那天已经是5月22日,在欢迎我们这批曾经是社会弃儿的迟到者的大会上,我喊出久久积压在心底的话“我们要读书!”台下许多老师和同学潸然泪下。那一年,我30岁,正是人生的而立之年。
我们的校舍条件非常差,环境也不够安静,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旺盛的求知欲望。因为我们已经失去的太多了。那是从一场伤痕累累的浩劫中刚刚复苏的年代,缺少好的教材,不少老师都是从一些资深的中学老教师中选调的,还有一些刚刚平反改正的老“右派”,他们对我们这些经历特殊,性格成熟的学生充满了感情。学习的日子充满了活力和张力,我们一个班40 多人基本分为两类人;一类像我们这样年龄大,饱经沧桑的老知青,还有一些是从农村考进来的应届生和复员军人。经历不一样,思想观点一时难以融合。我的同座罗立群比我小十岁,是白湖农场看押劳改犯的民警,人很倔强,但他能够将《红楼梦》中全部诗词背得滚瓜烂熟。有一次为社会发展的动力究竟是阶级斗争,还是生产力?他和我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要动拳头,但他却是我的老弟,我睡下铺,他睡上铺,引为知己。毕业后,他被分回庐江县一所农村中学任教,以后连续4年报考研究生,次次落第,我一次次鼓励他不要泄气,第5年他终于考上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小说史的硕士生。他现在是广东珠海出版社的总编,成为国内研究武侠小说的权威之一。来自寿县的姚弼是一位迂夫子,满腹经纶,写一手风流倜傥的好文章,在“文革”期间他因文字而惹祸,受尽折磨,他豪饮,每饮必醉。他能够将2000多行的《离骚》背诵得一字不漏。在溯风砭骨的冬晨,他戴着棉帽手套,踏着冰霜,在校园一角枯草丛中背诵古文。他佝偻的身影,抑扬顿挫的诵读,成为我们校园一道风景。30年来他一直在六安一中教语文,我读他古文韵味的来信是一种享受。我一面读书一面勤奋地写作,用稿费补贴生活。当我写的一篇介绍芜湖铁画的文章被英国广播电台采用,并汇来10英镑的稿费时,全班同学为我欢呼,我从银行取出那笔钱,给远在武汉的妻子买了一条羊毛围巾,,为自己买了一条裤子。然后和姚弼、罗立群一起去医院看望王纯才,他在篮球比赛中摔断了腿,已经治疗一个多月。我们将拄着拐棍的他拖出来,在新市口的一家小饭店里花5元钱点了三菜一汤和一瓶“弋江大曲”,举杯痛饮,祝福他早日恢复健康。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时期,进入文化复兴的时代。那几年的校园生活充满了生机,使人感觉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许多曾经被禁的书刊、电影片又重新开放,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看了法国影片《红与黑》,《巴黎圣母院》。交谊舞刚刚恢复,校园里荡漾着歌声,我们还自编自演了独幕话剧《心灵之歌》,它以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事件为背景,控诉“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人民的抗议,至今我还保存着这个独幕剧的油印说明书和剧照。许多许多新思想新思潮涌进校园:萨特的存在主义,武汉大学学生们编的杂志《这一代》,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等等。我们举行话剧《雷雨》的讨论,筹备编印小报《启蒙者》,我们积极参加各种比赛,我的散文《蓝色的梦》在首届安徽大学生作文比赛中获优秀奖。
1977年,中国的冬天是温暖的。中断12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如冬雷惊笋,如春风绿岸,一代人的命运发生巨大变化。全国有570万青年参加了这次划时代的高考,最后只录取了22万人。30年已经过去了,我们与共和国的命运一起沉浮,成为跨世纪的的栋梁之材。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正是邓小平这位伟大的历史巨人,以惊人的胆识,力挽狂澜,将我们这些曾经被淹埋在荒冢中的洁白石子--------共和国真诚的儿女们,重新发掘出来,镶嵌在新时代大厦的廊柱上。
1977年,党中央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是20世纪中国历史性变革的契机与先声。
我们正是这段震撼人心的历史的见证人。(2007年)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7: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7: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8:3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8:3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11:1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11:1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12:2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12:2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18:2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18:2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18:3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18:3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21:2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21:2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0 22:4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0 22:46: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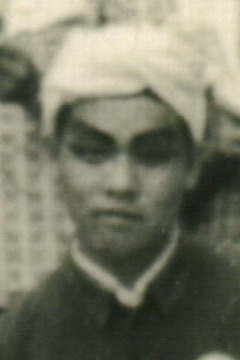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1 0:1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1 0:1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25 10:3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25 10:39: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