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草原上有过多次迷路的经历,不过今天记得最清楚的只有下面的三次:
第一次是在刚下到生产队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那天早上我到生产队队部找当时的领导班子主任满都拉谈一名知青插包的事,同时接到通知叫我到公社去参加一个会。我想:“刚从公社下来的,记得没什么叉路。”就一口答应下来。说完话,出门骑上我的那匹被队里人称为“铁马”的老马,向着认准的公社方向,信马由缰地出发了。不几步,突然一阵疯狂的狗吠惊到了我的马,那马立刻撒了欢在奔跑起来。我立时不辨方向地晕头转向起来,只能竭力控制着自己别从马背上掉下来。一会儿,大概是跑得远了,那条狗放弃了追赶回去了,我好容易勒住了马,开始辨别方向。奇怪的是,当时我们离开生产队队部、也是方圆几十里唯一的土房不过百十来米,房子应该就在我的视界之内,我却楞是什么也看不到。只能由着马儿缓步随意行走着,直到离房子不到十米的时候才突然看到了队部的所在。然后再从队部重新向公社出发。牧民们目睹了整个过程,背后一再悄悄地问其他知青们:“你们的‘答拉嗄(蒙语“领导”的意思)脑袋是不是有病啊?”
这次迷路还没有完。当我刚刚拍观上了一座山包,已经隐约能看到前面那座最高的坡,感觉再后面就是公社所在地的时候,我的老马突然无缘无故地发疯般拐向另一个方向飞跑起来。这匹老马是生产队唯一的“牧主”本人的坐骑,一直特别老实听话,所以生产队领导才专门连同牧主的一套银制鞍具一并配给了我这个知青的“头头”(因为这批知青是我亲自跑到的指标组织下来的)。老马一发威,自然是勒破了嘴唇都不停下来,我只好再次任它去跑了。一路横向(指与去公社的方向正好是90度的角,这当然是后来才知道的)奔跑,老马直跑到一口水井前才突然站下。我这才想起:自从那天这马分配给我,自己居然一直忘了给它饮水!可井边当时没有打水工具,老马站了一会儿,才极不情愿地移动身子,自动把我带到了公社。到了那儿给它饮水时,它居然一下子喝了三大水斗子(每个水斗子都和一般的洋铁桶差不多)!
第二次迷路是一帮知识青年一起迷的。
那是下乡第一年的夏天了,全队定于晚上集中到一户牧民家去开什么“划阶级”的会(当时批判乌兰夫没有对牧民发阶级成份)。散会时已经至少有十二点多了。七八名知青就商量着一起回生产队的土房子去凑合一宿,也好不耽误第二天的劳动---编柳笆(一种用来拦羊圈羊的用具。用柳条编成高一米二左右,长约一丈的样子)。
刚离开那个蒙古包不久,大家就集体迷路了。原因是通过一阵激烈的辨论,大家居然一致认同“月亮是从西边出来的”,佐证居然是“因为太阳才是从东方升起的”!这方向一反,根本就不对了。不一会儿连月亮都不见了,天地一片漆黑,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这下子大家可是越走越觉得不对劲。于是,我向大家讲了“老马识途”的事,大家就一起跟着我的“铁马”慢慢地走着。突然,我的马站住不动了,拼命看才发现已经到了队部土房子的后山墙。
第三次又是我一个人迷路。
那已经是初冬时分了。一场小雪把山川完全盖成了白色,地形地貌好像一下子全都变了样。
那天晚上,当马倌的知青老侯带着我去不远(也就二三里吧)的井边去饮马。我记得穿了一件羊羔皮的蒙古袍,脚下是镶牛皮的马靴。
当天的风很大。直从川里刮过来,送来了刚打下的青草的芳香。此时的山外,草已经全部枯黄,而山里的草却仍然有一丝绿意。但山里缺水,我们当时还驻扎在山外的漫坡处,只有等头场封山大雪下来后才能搬进山去。所以,当我们饮完马准备回自己的蒙古包时,老侯很不放心地问我回得去回不去(这时他早已翻身上马,我却还在哆哆索索地在勒马肚带)。我想这么几步路应该没有问题,就让他先走一步。也就过了五六分钟,我也上马了。刚跑几步就觉得不对劲。这时我骑的不是那匹识途的铁马,而是给我配的另一匹小花马。这匹马有腰身很软,骑上去非常舒服,就是不大听话。此时它喷着响鼻,冲着草山的大路狂奔起来。我明白它也是闻到青草的香味了,所以才那么不听话的。幸亏这马的嚼口软,不几下就被我拉得转了向,乖乖地听我摆布了。可这时我却找不到自己的蒙古包在哪了。月亮只有一牙,星星也非常稀少,天好像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那些平常已经相当熟悉的山坡好像都成了一个样子。徘徊许久,我终于放弃了努力,下马把缰绳和嚼子摘了下来,再解下自己长达三丈的腰带,连成长长的一条,一头仍然笼在马头上,一头拴在自己的手臂上,给马上好了脚绊子,让它在一旁啃草,我则卸下马鞍,挡在风头处,自己把皮袍脱下横铺地雪地上,再把自己裹了进去,就那么睡了小半宿。等到天开始亮了,我才发现,原来离自己的蒙古包只差了一道山梁。幸亏那天不算太冷,我睡的又是个背风的斜坡,不然估计今天就没法给大家讲这个故事了!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6/9 21:4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6/9 21:4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6/10 17:3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6/10 17:38: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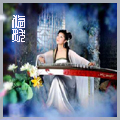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6/11 11:1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6/11 11:1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31 14:2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31 14:2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8/7/31 14:5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8/7/31 14:5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5/10 21: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5/10 21:4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5/10 22:2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5/10 22:2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5/10 23:4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5/10 23:4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5/11 0:0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5/11 0:0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5/11 8:3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5/11 8:38: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