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香
陆翀
一
一口香,俗称羊棒,据说是蒙人留遗下的。这种用羊的腿棒骨制作的烟管儿,在后大套极普通。
冬三月,日短夜长,男人们凑在灯前消闲——那当炕亮着的油灯,大多是用学生娃娃的空墨水瓶儿自制而成;缠上一截儿细铁丝,把小瓶儿固定在尺半高的木头削成的灯柱儿上;燃煤油,比起当年用残破渍垢的灯碗儿,“麻油油点灯半炕炕明”的光景,显见得是一大进步了。——当然,要是闹饥荒,没钱买煤油,就得续添从加工厂、机耕队淘换来的废柴油;那可就免不了烟气大,觉见呛了。
人们左手持羊棒,右手伸出拇指和食指,探进烟钵钵,捏起一撮烟丝(原是经过特制,压成板状,包在油纸里的。只是,贵贱得花钱买回;近两年钱紧,人们多以自种的烟叶,揉碎代之),借着手汗的潮气儿,揉成不大大的烟球,往羊棒的铜泡儿上轻轻一按,就着如豆儿的灯火点着,深吸一口,再把羊棒朝外首偏下稍微一转,猛地一吹,烟球儿的余烬,便“啪”地一声窜出铜泡儿,沿着抛物线的轨迹,流星般地陨落在黑暗中了。那眯细着眼睛深深吸进的一口烟,香彻心脾,所以,人们又冠之以雅号,美其名曰“一口香”。
就这样一吸一吹地、一口接一口地“香”着,又解瘾,又解闷儿,越抽越来神儿。寂寞寒冬的长夜,劳顿三夏的黄昏……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又一年,就这样一吸一吹地,不知不觉地打发了。
人们贪恋这一口,倒不全是为了消闲。后大套苦重,挖渠苦,淌水苦,……劳苦倦极,抽上一口,解困乏、去湿气。烟油子味儿冲,夏天在野滩上,还可以防咬驱蚊,连蝎子也不敢近身。羊棒用得年长了,磨操得光溜溜地,骨髓腔里渗满了烟油儿,看上去紫红透亮,如红玛瑙一般,煞是喜人。早年间,歹毒的地主还劝诱长工抽大烟。风里雨里,场里地里,吆牛断马,犁锄耙磨,一年下来,只给几两大烟土。老李庚的爹就是抽上大烟后,闹得营生也做不成了,还欠下一屁股债,临了被地主邬二毛赶走。那年,李庚虚岁十四,是被扣下抵债的。
二
一九六八年是我在召圪台插队的第三年。入乡随俗,晚饭后,到老乡炕头上盘腿一坐,边抽烟,边闲扯,已是常事了。有一回,听说东营子老李庚家里,有支用鹰翅膀的骨管儿制作的“一口香”(或可由“羊棒”一词移用为“鹰棒”),普通的羊棒,尚且如红玛瑙一般紫红透亮,流光溢彩,用鹰翅膀的骨管儿制作的“一口香”,想必别具一格,更加瑰奇了!更何况这“鹰棒”的“一口香”,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是方圆百里的唯一!我忍不住心痒难耐,便特意前去见识见识。
召圪台坐落在两狼山脚下,五家河南岸,因早年有座召庙而得名,如今召庙早已不见了。据说最后的胜迹全无,是大炼钢铁那年,就地取材,抽撤柁檩,拆卸门窗,点了土高炉了。就连颓垣断壁的砖瓦土坯,也全都应急于垒砌土高炉之需了。召圪台只有东西两个村落,六、七十户人家。老李庚是队里的五保户,家在东村(当地老乡习惯叫做东营子)紧东头儿的沙梁上,两间土坯房,虽然也是解放后盖起的,可咋也有十大几年了。从打度荒过后,这二年,“四清”工作组、生产队统一规划,东村新盖起的一排排玻璃门窗大正房,全都不断地往西靠拢;老李庚的小屋,残留在旧村落的废墟中,就显得孤僻而鄙陋了。
“李大爷在家吗?”我招呼着推门进去,屋里黑黢黢的,炕头亮着盏自制的小煤油灯,灯火如豆,映着蒙尘挂灰的四壁,就更显得暗淡无光。老李庚满嘴酒气;灯下,光亮的秃脑门儿汗津津的,黑红的脸膛越发红了。他兴冲冲地把我让到炕上,很自己地递过羊棒,把烟钵钵推到我跟前。
“你大爷我打了一辈子光棍儿,痛快了一辈子!”显然,用句时兴的话说,他是把我当作“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了。这也难怪,当初,县安办的领导勉励知青:“安下心,扎下根,养下娃娃抱上孙……”我们听了,颇不以为然。近二年,社员里有人在背后,冷言冷语地编排知青:“一个人吃了,全饱了;挣下两个,管好了;超下支了,偷跑了;老了老了,五保了。”看来我们知青是命里注定要打光棍儿了。我一手拿着羊棒,一手揉搓着烟叶儿,却没有抽。抬眼只见,老李庚正笑吟吟的注视着我,粗眉下的大眼,闪着慈爱的光,眼角儿满是鱼尾纹儿。
“你们这些学生娃娃,从大地界到咱这穷乡村,不易呀!”老李庚摇摇头,那神情,像是在赞叹,又像是爱莫能助的矜悯。愣声半晌,又不无遗憾的说:“你这后生,干是实干了,可就是有罪没苦;不像你大爷我,是从小儿在庄户地头跌打出来的。”他说的“有罪没苦”,指的是能够受罪,可就是干不出活儿。幸亏那年月“大呼隆”,打混工,像我这样的,好歹还能混出个口粮钱。我知道,老李庚年轻的时候,五大三粗。听说那咋晚儿(那时候),他壮得能够一膀子把牛抗倒。
[待续]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3 18:3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3 18:39:00 [只看该作者]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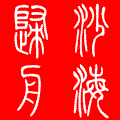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3 19:0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3 19:0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3 20:4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3 20:4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3 23:3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3 23:3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9:5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9:52: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11:3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11:3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13:1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13:1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14:5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14:5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15:3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15:3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2/24 15:5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2/24 15:52: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