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不栽树
唐人诗云“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那可是真的。我所在的五师地处临近蒙古的西乌旗,那年九月二十三号(农历八月)就下了第一场雪。这标志着草原上实际意义的冬天已经降临了。
初冬没有那么紧急的劳动任务,连队会选一个好天派一些人到山上拉椽子。
连队西北方几十里的地方有一座山(可惜我忘了名字),山不高,但山丘绵延起伏,山上植被特别好,长着密密麻麻野生的白桦树。不知它们树龄几何,都还不足碗口粗,却成了附近几个连队重要的建筑材料。
白桦落叶时节,连里就派了七班上山砍树。这个七班在我们连算得上响当当的优秀集体,班里十二个女战士,个头差不多,个个英姿飒爽精干巧慧,干什么工作都追求卓越,以敢打能打硬仗闻名全团,而她们的内务又是最规范最整洁的。
这些女兵精神抖擞上了山,白天出去砍树,晚上就住在山下的蒙古包里,十几天下来成果斐然。
跟大车去山上拉椽子,是我非常喜欢干的活,一天一趟活不累,还可以顺便观赏野外风光。上山需要做一点小准备,每人要穿高腰雨靴,因为山上的雪很厚,当然为了防止脚冻伤最好里面要穿上毛线织的厚袜,还要拿上能捆椽子的背包带。早饭要多吃一些,因为到下午才能回来,午饭没地方可吃。
几辆大车载着穿着棉装的男女战士在白茫茫的雪原上疾驰,天不算冷,没有风而且阳光灿烂,每个人看上去都兴致勃勃,一路谈笑风生,像是要赶着去看大戏。
没有想到雪后山景这么美,竟有神奇的雾凇!大树小树都粘缀着雪,有的像梨花冰清玉洁,有的像银条玲珑剔透,有的像白菊蓬松绽放,还有低矮的荆棘杂草,一簇簇一串串一团团毛茸茸亮晶晶千姿百态;大小丘陵土堆都披着霜裘雪氅,或卧或站或驼仙翁神叟一般,真是一个粉装玉砌的童话世界。我立即联想起了以前读过的苏联小说,那浪漫的白桦林、厚厚的积雪、美丽的故事……
有男生扯着嗓子在唱了“……好一派北国风光……”,哦,高音上不去,走调了,但眼前情景与唱词中情境还真有些相似呢,没想到如今咱也有缘体会一把 “战严寒化冰雪胸有朝阳”的意境。
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盖在雪下面被砍倒的树拖下山来。大家争先恐后踏着厚厚的积雪爬上山去,拽出一棵棵树,码在一起用背包绳束紧扛在肩头或搂在腋下顺坡往下走。
这个工作的难度在于放倒的树总是东一棵西一棵的比较分散。当时不解,后来听人说在森林里砍树不可以挨着砍倒一片,必须有间隔,这样森林虽比以前稀疏但整体依然存在。更大的难度就属于路线问题了,山上本没有路,残留的尖利树桩就藏在雪下面,如果选路不对就会被树桩拽住树枝动弹不得,还极有可能被扎破鞋子伤了脚。开始大家小心翼翼,摸索前进影响了速度,后来走的人多了,共识自然形成了,一条合理的雪道应运而生。人七扭八拐走在前面,树捆拖在后面,就坡下势优哉游哉,树捆越来越大,速度也快了许多。
下午太阳刚刚西斜的时候,几辆大车就已经装满,大家在车上面爬着坐着唱着,胜利回返。车走得很快,一会那山那林就被渐行渐远的我们甩在身后,回头望去,白雪散落脚印杂沓没拉走的树横七竖八,那圣洁那静谧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是一片狼籍。
连里的空地已经堆满了砍来的白桦树,较粗壮的要刮净树皮留做盖房的椽子,剩下的枝杈,大家用来生火,——非常好用,那树的皮沾火就着。
连里院子好大,一棵树都没有,没有人想过要栽树。我们热火朝天地砍树拖椽子刮树皮盖房子生炉子,而那时,我们的确没栽过一棵树。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2 11:5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2 11:5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2 12:4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2 12:49: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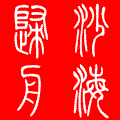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2 13:4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2 13:42: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2 13: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2 13:4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2 16:5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2 16:5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3/13 9:2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3/13 9:24: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