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爷去年跑了两个马拉松,一个是郑州马拉松,另一个是北京马拉松。郑州马拉松是我陪他去的,当时,秀儿和她女儿在当地负责接待我们。
去年四爷五十四岁,两次跑完业余组全程马拉松,时间都是三小时五十几分钟。据说,在他这个年龄段,只要在四小时以内跑完全程,就算是好样儿的。
元旦前两天聚餐时,四爷在餐桌上宣布;他要参加2008年1月5日在厦门举办的国际马拉松。
大家问:“你一个人去?”
他看看我说:“去那么远的地方跑马拉松,谁肯陪爷去?爷只能一个人去呗。”
“行了,行了,别装可怜啦,”我说道,“爷陪你去还不行吗?正好那两天,爷也没什么事。”
四爷见我又一次答应陪他到外地跑马拉松,高兴得一脸灿烂,说他来负责买机票,还问我厦门有没有认识的好朋友,如没有,他则给当地驻军打电话,我们便会得到很好的接待。我说,先不忙给人家打电话,等我回去翻翻名片再说,记得在厦门我是有熟人的。
还别说,回家一翻名片夹,还真找到个叫薛达镇的住在厦门的朋友。
薛达镇是台湾学者,受聘于厦门高校教书。他曾到北京跟我们谈过一个合作项目,期间,用餐时,他说他不喝啤酒、葡萄酒,只喝高度白酒,一下子就获得了我的好感。
电话里联系上了达镇,他非常高兴。“薛老师,”我对他说,“这次去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就是单纯地跑个马拉松。找你,图的是我俩在厦门,不想有举目无亲的感觉。”
电话里传来哈哈大笑声:“我让你俩来了,感到举目即亲行不行?”
四爷买的是最便宜的打折机票。我俩3日晚上九点从首都机场登机,一百多个座位只稀稀拉拉坐了十几个乘客,空中飞行那段时间,四爷得意地说:“威不?这架飞机多像咱俩的专机。”
崩溃!原来这世界上还有比我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呢。
达镇和他的中学老师简教授在厦门机场等候着我们,大家见面热烈握手,然后由达镇开车,把我和四爷送到了下榻的宾馆。
达镇让我和四爷睡个好觉,说明天上午他开车来拉四爷去组委会报到后,再乘车实地跑一圈马拉松的路线,使四爷对地形了如指掌。
第二天,天朗气清。上午我们陪四爷报了名,领了运动服、胸号和磁片,看了路线,中午大家一起用餐。午休后,四爷继续睡他的觉,我则带上笔和印章,由宾馆溜达到达镇的工作室,开始挥毫泼墨,答谢达镇及简老师的热情接待。
简教授本来就是大学者,同时又是诗人兼书法家,我边写字边跟他交流书法心得,谈得其乐融融。
达镇说:“书法不是人人都写得来的,我试过,发现我就不是写字的那块料。所以,我早就放弃写毛笔字了,只当一个欣赏者。”
我说持达镇这种观点的人很多,但我有不同看法:“毛笔字是人人都可以写好的,最要紧的是学字的人能否碰到一个会教的老师。碰到了,学生只要按老师吩咐的步骤去做,就绝对能写好字。我教过的学生中,有的是写字基础很烂的,但经过正规训练后,现在照样都写出了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关键是要碰到会教的人。”
就这么聊着天,我用草书写好了一张八平尺的《爱莲说》。此时,正好进来一位气度雍容的大姐,两位教授立即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台商前任厦门协会的会长张大姐。这位是北京来的兔子老师。”
我跟大姐握了手,说:“大姐,在下正在试笔,如蒙不弃,这幅草书就送给您结个缘吧。”
张大姐喜出望外,连说:“感恩,感恩!”
接下来,我用自己去年刚发明的“抖绸子法”,给简教授写了一幅《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张大姐信佛,我边写,她边在一旁感叹:“兔子弟弟,这么轻松就把《心经》一字不错地写下来了?”
我说《心经》早就长在我脑子里了,何时写都不会出错的。
写完了《心经》,我问达镇:“你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嗨!”他叹了口气,说,“我家是农村的,爸爸认为我能出息地当上镇长就不错了,于是起了这么个名字给我。”
我哈哈大笑,说:“那给你写个藏名联吧,上联是:‘达观不计皮毛事,’下联请简教授给出一个吧。”
简博士略做沉吟,随口说道:“下联就写:‘镇定方成栋脊材。’”
当张大姐知道我是专程陪朋友来跑马拉松的,表扬我是个讲义气的人,说她有明天坐主席台的胸卡和能够直接进入赛场中心的车证,晚上她的商务宴会结束后,就给我们把证件送来。这样,我们开车出入马拉松的场地就方便多了,可以不受警察戒严的限制。
这次,轮我连说:“谢恩,谢恩!”了。
就这样,次日,四爷在三位台湾朋友强有力地支援下,顺利跑完了马拉松全程。用时:三小时五十六分整。名次:第666名。
<!-- -->
(完)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1:2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1:2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2:3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2:36: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3:0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3:03: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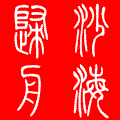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6:4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6:41: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8:1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8:1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19:52: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19:52: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21: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21:4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3 21: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3 21: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4 9:00: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4 9:00: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09/8/4 9:36: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09/8/4 9:36:0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