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读“白发狂夫《格律诗词》我之拙见”之我拙见
春节期间,我因忙于家事,疏于上网,远山近水弟告我在诗词版块又读到一篇好文章:白发狂夫的《格律诗词》我之拙见。我先是看了一遍,这是一篇很有学术性质的文章。昨天晚上,远山近水弟与我Q聊,再次谈到“白发狂夫”的这个贴,有些遗憾地说,这篇文章跟贴者却寥寥无几,显然是“高处不胜寒”了。
今天再次浏览中知网,看此贴,狂夫兄又贴出一篇下文,而且,见广西知青跟文说的倒是中肯。在中国古典诗词上,广西知青总能坦诚相见,不一味迎奉,能有这样的诗友,该是荣幸。
我一直都对中国的格律诗词“畏律如虎”,但因为毕竟傍听过一些“古汉语”及古典文学的课程,所以还算“观虎知皮”。
并且因为文革和插队及个人的爱好,把发表的毛泽东诗词竟背得滚瓜烂熟,而在一九八三年的那个年代里,改革开放刚刚启步,对文化领域并未触及很深,所以老师讲古典文学之诗词及格律诗词,大都以毛泽东诗词为主,间以古人的名作。就律诗来讲,老师给我们解析过《七律·长征》
现在查百度,仍可得到如八三年的答案: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诗歌典范,它既写出了红军长征所经历的千难万险,又把红军为了实现北上抗日的革命理想而排除一切障碍,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发挥到极致,达到了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统一,可以称之为艺术精品,千古佳作。
唐朝与宋朝取得政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式。一个是“隋唐演义”,而另一种是“黄袍加身”
受政治影响,在文学上产生了各异:所谓“唐诗宋词”,唐人赋诗,宋人慨词。唐人的诗是从古风渐渐朝格律发展,所以,盛唐、中唐、后唐诗作风格各有千秋,决不遵律。用唐—崔颢:《黄鹤楼》例,严格地说,这是盛唐时代诗人崔颢的一首著名的七言诗(而非七律),关于这首诗有这样的说法:《唐诗纪事》里记载说,传说李白游黄鹤楼读到这首诗后大为佩服,曾慨叹地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最后是李白“无作而去”。据说李白游黄鹤楼时也曾试作七律,欲与崔诗一较短长,而终未能成篇,才作此叹语。这可由李白的《鹦鹉洲》诗与好几年后写成的《登金陵凤凰台》跟崔颢的这首《黄鹤楼》诗的风格近似去确认这一点。这首诗究竟有什么奥妙能使诗仙李白也为之折服?并且宋代严羽的《沧浪诗话》更推为“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语,如果从律诗的角度去看,此诗并不符合格律的要求,前半段是古风,或半段才与律诗格律相符。内容上也不是很大气,至少不令人奋进,消沉和颓废的情绪笼罩着诗人,也笼罩着读者千年。严羽如此高捧,这是与宋朝的政治气候有关。
到宋朝,诗词已经有了分化,既婉约派和豪放派,这是任何一个研究宋代诗词的人都应该明白的最基本知识。
而毛泽东诗词在继承了建安文学苍凉刚劲和宋代“苏辛”豪放派风格的基础上,以自己独特的伟人胸襟和植根于民间的丰富语言,开创了历代作家所没有达到的“大气”“开阔”“雄浑”“磅礴”而又幽默、洒脱的艺术风格,把中国豪放派诗词创作推向新的高峰。其作品也代表中国现代诗词创作的最高成就。毛泽东要求文艺家“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毛泽东诗词正是运用这样的世界观分析和表现社会生活的光辉的典范。
所以,既使是格律诗词,还是以意境、胸怀、气势、才华为主,单一的以格律墨守成规,终究不会产生好的作品。
对于狂夫兄所言:“打个比方,一个人的声音不怎么好,任其脸蛋多么漂亮,也无法掩盖其音质的欠美。”此例似有偏颇。关于声音与脸蛋不可同一而论,至于音质好坏更与写格律诗词毫不相干。唱诗词用声,写诗词落字。而词谱也好,韵谱也罢不是根据音色音质而遑论,而是以形式上的格律、字面上的声韵而订谱。既“统字规音”。
并且,声音好坏,你怎么标准界定?是洪钟大吕为好声音,还是吴侬细语?是钢锵有力,还是靡靡之音?除却专用场合、表演之外,能讲一口溜利的普通话交流既可。不管对朗诵家还是歌唱家都不可能为了表现自已的好声音和好音质而一说话就来个抑扬顿挫的“啊——”;或用唱歌的低音、中音及高音讲话。所以,这种例子是不能成立的。
因为写诗词不是听评弹。
不知狂夫兄是否喜欢听评书?而在改革开放初期,曾有一段时间有一些人简直对评书着了迷,特别是对单田芳的评书更是达到了痴的地步,他们说,就好听单田芳的“哑嗓”,具有独特魅力。那这种沙哑的声音算好听还是不好听,对于艺术中的美学,如莱辛所讲:“一切艺术皆是现实的再现和反映,都是“摹仿自然”的结果,这是艺术的共同规律。”见莱辛的代表作《拉奥孔》;副题是《论诗与画的界限》。在这篇文章中,莱辛从比较“拉奥孔”这个题材在古典雕刻和古典诗中的不同的处理,“论证了诗和造形艺术的区别和界限,阐述了各类艺术的共同规律性和特殊性。”
北大的古汉语老师曾经讲过:中国的格律诗篇很少有大作,特别是七律这种格式,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是《念奴娇?赤壁怀古》词、“怒发冲冠”是岳飞的《满江红》词、而南宋著名的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文天祥留下的《过零丁洋》千古绝唱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首七言诗是文天祥被俘后为誓死明志而作。是一首永垂千古的述志诗,而非尊格守律的蹀躞诗篇。所以既没有对称,也不求平仄,只是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了。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遭遇。国家民族的灾难,个人的坎坷经历,以及壮志未酬的复杂心情,这时候,诗人决不会再去考虑什么格律诗词的清规戒律。所以毛泽东的几首七律都可以说引领风骚。与狂夫兄开个玩笑,文天祥在过零丁洋时,决不会推敲“第五个字往往是‘诗眼’,其平仄声调显得同样重要,不能轻易放宽。因而更为科学、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一、三可不论,其余要分明’。”
以文天祥的诗词造诣不会低于那些谙熟格律诗词的老知青人。并且,文天祥是宋灭之人,这时,虽然大宋灭亡,但格律诗词已经成熟,并且有了《平水韵》谱。其实,平水韵谱的编纂者刘渊是金国人。南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壬子年(公元1252年,此时金已亡于蒙古),刘渊只好到宋朝庭考官,可能在南宋礼部任职,他曾编写刊行过新的《礼部韵略》共107韵。(此书已佚失,只能从元初黄公绍、熊忠的《古今韵会举要》一书瞭解到一些概况)。与北宋仁宗景祐四年(公元1037年)发布的206韵的科举考试用官韵《礼部韵略》不同,新的《礼部韵略》和王文郁的106韵的平水《新刊韵略》是一致的。元初的阴时夫著《韵府群玉》定名106韵的版本为“平水韵”。明代以后文人则沿用106韵。所以,身在朝庭做文官的文天祥不会不知道这部〈礼部韵略〉,但写“过零丁洋”时,大宋江山早已换了国号,所以,国之不存,礼之贻尽。
不过,乱世藏金,盛闹玩文。所以,现在一对“核桃”竟能值十万八万。也就有了讨论“格律”的雅性。白发狂夫的这篇文章——《格律诗词》我之拙见该是百舸之首。能引领此版块谈诗论词之风尚为好。
而“之我拙见”方为拙见,算是响鼓一击。
静春惶写于正月十六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2 12:3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2 12:34:00 [只看该作者]
 [本帖被加为精华]
[本帖被加为精华]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2 16:53: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2 16:53: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3 15:21: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3 15:21:00 [只看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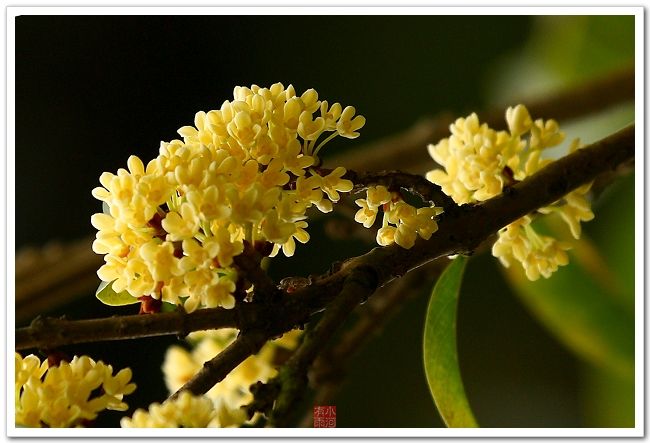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3 21:5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3 21:58: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3 23:2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3 23:2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5 15:15: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5 15:15: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5 22:09: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5 22:09: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5 22:24: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5 22:24: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5 22:47: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5 22:47:00 [只看该作者]


 加好友
加好友  发短信
发短信

 Post By:2013/2/25 22:48:00 [只看该作者]
Post By:2013/2/25 22:48:00 [只看该作者]
